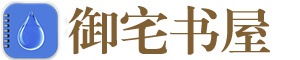32
作品:《有待确认》 过年期间忙碌不可避免,沿袭了几千年的习俗彷彿都得要挤在这短短几天实行,一下是不能打扫,一下是不能洗衣服,说错话了得说童言无忌,东西碎了要来句岁岁平安。培青不喜欢和亲戚寒暄,没过多久就不见人影,剩我和一干堂兄弟姊妹吃花生聊天。
聊天的话题不外乎是围绕在小时候的趣事,或是自家爸妈的事,起初我还听得津津有味,但后来实在是难以对自己做过的事如数家珍,藉故离开。要回房间休息经过书房,培青坐在里头盯着书柜里的奖状发楞,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回过头,将我拉到她身边。
「看,你以前说故事比赛奖状。」她轻声说,「优等耶。」
我凑近看,发黄的奖状纸上以笔墨勾勒出故事题目和我的名字,而我看见题目后失笑。「『离群索居的鲸鱼』?我居然说了个鲸鱼的故事?」
培青煞有其事的点点头,「一听就是个充满文艺气息,而且又有点哀伤的故事。」她假惺惺的把手斜斜伸直,惆悵的蹙起眉,煞有其事,「『从前从前,有一隻孤独生活的鲸鱼,牠的一生除了无尽的海水和蜉蝣外,什么也没有』。」
我不以为然瞄了她一眼,「……刚刚在大伯面前就没看你这么活泼。」
「啊,我真的很不擅长跟长辈相处啦。」培青噘起嘴,把头靠在我肩膀,「我还记得你这次比赛,我们全家都有去看,还拍了你领奖的照。那时候还有人穿鲸鱼装演鲸鱼,在你说话的时候,躺在舞台上学鲸鱼游泳的样子。」
「那他演的鲸鱼游泳是什么样子?」
培青眉开眼笑,「他从头到尾就只是躺在舞台上闭着眼,动也不动像隻死鱼一样。」
我下意识要潜入脑海攫取这段记忆,不过结果总是徒劳无功。那一大片深海一如既往漆黑难以辨清方向,即使培青说得绘声绘影,但那画面像是老旧的八釐米电影画面,忽明忽灭。
培青后来说要找那张照片,东翻西找,一下子整个房间变成她的宝窟,她翻得不亦乐乎。
我蹲在一旁陪她找,「都那么久了,应该弄丢了吧。」
「你又还没找怎么知道找不到?」培青弯腰埋首在一叠叠旧物中摸索。
我叹口气,转身在另外一边的柜子搜寻,途中因为旧物扬起的尘粒打了好几个喷嚏,但我实在没找着,剩下的全是很小时候的作业本或是相簿。我坐在旧杂志扎成的小方砖上,看培青埋头苦干。
「任培青,要不要等等再找?先出去吧。」
培青动作停了下,之后继续忙碌,「不行,一定要找到。」
我嫌她太拼命,「只是张照片而已,不用这么努力。」
「……但要是找到了,对你来说,一定不只是张照片。」培青用手随意摆弄找完的书堆,转往下一个目标,继续翻弄,「我知道你对国中那件事一直没有释怀。然后妈也是,她的保护慾有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变态的程度了,换作是我也会感到难以接受。所以上大学以后,你才这样不常回家。」
我因为过度讶异,一时之间话梗在喉头说不出来。我从来没和培青说过这件事,我认为那与她毫无干係。
我垂眸拨弄固定书籍的红色尼龙绳,「不是。我不是因为讨厌那样的妈。」
培青蹲在地上,侧身等待我的回答。
「我是讨厌让她变成那样的自己。」我的鼻子开始泛酸,于是深深纳入一口气,想以此消退攀升的哀愁。「那件事情跟她没有关係,她却把那件事故认为是自己失职,不停把它放在心上当成是惩罚。」
静了良久,培青才喃喃,「姊……」
「其实要是我再勇敢一点,可以在事情发生不久后大声跟她说,『妈,这不是你的错』,或许她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这些话让我将辛苦建构成的墙砸出一个大洞,我的眼泪于是不听使唤淌下脸颊,「你知道吗,或许我那样子做了,一切就会有改变。」
培青只是默默不语持续找着,后来她轻轻「啊」了声,低头盯着找到的照片一会儿,慢慢开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她把照片递给我,「像那样久得只能从照片缅怀的事,再计较有什么用?」
我接过手,手背抹乾眼泪,照片里的我手伸得老直,站在麦克风前,眼睛闪闪发光。而在我脚边则是躺着一个穿着纸製鲸鱼装的男孩,他仰躺着,双眼紧闭,由于时间久远,照片里的轮廓因为泛黄而显得模糊。
「可是虽然这么说,那还是你最在乎的事,所以我想要是能帮得上你什么就好了。」培青从身后拥住我,「以前我太小,不懂得太多,不晓得你跟妈为什么要像隔着一层膜一样对话,不晓得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抱你,不晓得为什么她不愿意跟你谈起以前的事……可是现在我长大了,该懂得都懂了。」
我扯出一个难看的微笑,眼泪因为弯起的眼而再度滑落。
「姊,我会努力帮你找回记忆,不过我希望你也知道,你们谁都没有错……」
我吸吸鼻子,但培青的话宛如一把钥匙,打开我心里那道锈了十几年的锁。当我转过身紧紧抱住她放声大哭时,我听见那道锁轻轻被开啟了,声音短促而清脆。等我哭得甘愿,代表培青的衣服也湿得差不多后,我和她两个人一起研究那张照片。
我们试图学福尔摩斯从照片里的蛛丝马跡推论,培青认真回想,只知道那时我有抱怨过那个男孩爱出餿主意,可是最后我还是乖乖就范,听那男孩的话,让他就这么躺在舞台上演起戏来。
我立刻联想到回来时在火车上做的梦,我是挺相信过去的事情会以这种方式回到人身边,不过我实在想不到它要告诉我什么事情……但我想如果把这线索丢给孙絳文,他会很乐意替我解答的。
我瞄了培青一眼,她完全不晓得我已经遇到孙絳文。
「欸,妹啊,我好像没跟你说过,我交男朋友了。」
培青惊喜的笑开嘴,「哈!终于!恭喜你结束两年空窗期啦!」随后她换上忧心忡忡的脸,「这次你不会再辜负人家吧?」
为什么我妹会跟简智雨说一样的话?不过现在不是吐槽的时候。
「辜负是一回事。」我併紧双腿,低着头,喉咙有些乾涩,「我想跟你说,那个人,是我的国中同学。而且他极有可能是害我失去记忆的那个男孩……」
培青脸上一片空白,失神望着我,宛如我说的话对她来说是天方夜谭。而后她总算找回神智,艰涩的吐出感叹,「哇……好复杂。但你怎么确定是他?」
我统整一下思绪,缓缓跟她说和孙絳文相识的经过,还有这些日子来他的欲语还休,以及我逃避听他认罪似的自白。
我在她面前毫无保留,事实上,也没什么好保留。事实就是那样,只隔着一张纸,端看人要不要伸手戳破探个究竟而已,只是到现在我有点搞不清楚,这样子一再拖延是慈悲还是残忍。
培青观察我一会儿,「你很喜欢他吼?」
我一时之间还真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愣了好几秒鐘,直到想起孙絳文那暖得能融冰的嗓音和柔和的目光,一种后知后觉的真实感才由心底深处涓滴而生。
「……喜欢。」我頷首,「我喜欢他到连想到他哀伤的样子都感到害怕。」
培青脸颊抵着手臂看我,「我猜你应该知道他哀伤的理由是什么。我跟你说,你不敢开口的那些话,时间一长,就会真的变成说不出口的秘密,就像你和妈这样。你应该不希望跟你男朋友也变得有口难言吧?」
我真想像起和他两人如同隔着一片海洋的拥抱,只是这么想,便觉得焦躁难耐。我摇摇头,没再说话,心里想着或许不该再让孙絳文隻身一人守候那过于荒凉的海域。
我想和他一起耽溺在那片时光里,浮不出水面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