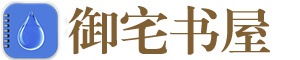前传(八点五):嫉妒
作品:《北境之笼(禁脔文学)》 嫉妒的藤蔓在百合子荒芜的心田悄然疯长。
这并非出于对尾形百之助本人的情爱,那点被联姻点燃的微弱火苗早已在他日复一日的冰冷疏离中熄灭殆尽。这份啃噬着她的嫉妒,更像是对一种“存在感”的渴望,一种对“被看见”、“被珍视”的扭曲向往。而这份向往的对象,竟直指向那个被安置在西翼、比她小了快五岁的异族少女——明日子。
每当百合子独坐枯寂的院落,听到西翼那边隐约传来孩童脆生生的笑声,或是年轻女子带着奇异音调、语气却无比自然的呼唤声,她的指尖便会无意识地收紧,掐进掌心柔软的肌肤里。一种尖锐的酸涩便如毒液般弥漫开。
凭什么?
凭什么一个本该处于“卑微”之地的外族女人,一个如此年轻就……她不愿去想那骇人的生育年龄,那个被抱在怀里的男孩“明”本身就是某种冲击……可以活得如此……真实?
嫉妒夹杂着一种更深沉的羞恼,让百合子坐立难安。她开始像着了魔一般,利用“主母”身份那点残存的、未被明确禁止的权力,在不越界的前提下,更多地“观察”起西翼的风吹草动。她端坐在茶室,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通往西翼的回廊;她借口巡视庭院,步伐总在距离西翼最近的花木处徘徊。
一次,当她带着侍女行至西翼外一处用于观赏的微型枯山水园,假装赏玩新修剪的矮松时,无意间瞥见了一幅让她心跳骤停的画面。
纸门半开的宽敞和室边缘。
尾形百之助随意地倚靠着一根廊柱坐着,身着居家的深色素纱单衣,手里拿着一卷摊开的书,眼神却并未落在书页上。
而阿希莉帕——就伏趴在他的腿上!
她穿着一件质地柔软的米白色浴衣,松散的腰带勾勒出她年轻身体柔韧流畅的腰臀曲线。因为伏趴的姿势,圆润饱满的臀峰在薄薄的浴衣下展现出惊人的弧度和弹性。她枕在尾形的大腿上,大半张脸被垂落的黑发遮掩,但能看到她光洁的额头和微闭的眼睑,神情放松而恬静,仿佛沉浸在无虑的梦中。
尾形的一只手搭在她线条优美的腰背上,另一只手轻轻放在她圆润微翘的臀侧上方靠近腰的位置,并非暧昧的揉捏,更像一种庇护性的圈揽,一种对所属物的自然覆盖。
阳光透过庭院树影,斑驳地洒在他们身上。阿希莉帕趴伏的姿态像只慵懒餍足的小猫,享受着一份她全然信赖的温存。尾形低垂着眼睑,目光落在她那半露的发顶和颈后,深邃的眼底没有了往日的算计和冰冷,只剩下一种近乎平和的占有欲,如同在审视一块专属于自己的、无价的温玉。
这画面如此自然,又如此……亲密,带着一种不容任何人打扰的安稳。
百合子像被钉在原地,浑身的血液都涌向头部。她几乎能听到血液在太阳穴里奔流的轰鸣声。指尖冰冷刺骨。巨大的冲击并非来自视觉上的“不堪”,而是那种无声流淌的亲密感。
那份自然的贴近,那份毫不设防的依偎姿态,尾形眼中那专注到极致却又毫无攻击性的……温和?那种在她面前从未流露过的、仿佛整个人都因怀中的躯体而卸下冰封铠甲的氛围……所有这些,都如同淬毒的钢针,狠狠刺穿了百合子精心构筑的堡垒。
原来……那个阴郁深沉、如同阴影般盘踞在她丈夫位置上的男人,在面对她时,也可以有这样的……松弛?
强烈的嫉妒混合着巨大的失落,瞬间让她头晕目眩。她死死咬住下唇,用尽全身力气才没让身体颤抖得更厉害。她强迫自己收回视线,转身离开,步伐甚至比来时更匆忙僵硬。身后侍女疑惑的目光像芒刺在背。
那画面如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在了百合子的脑海里,在夜深人静时反复灼烫着她。
而真正让她感到窒息、让她连最基本仪态都几乎崩溃的经历,发生在几天后一个沉闷的午后。
宅邸里的大部分仆人都去准备几天后一项重要的家宴。百合子在自己过于空旷、整洁得令人心慌的院落里枯坐良久,只觉得空气沉闷得无法呼吸。鬼使神差地,她起身走向西翼方向,内心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想去看看修缮园林的进度。可当她走到连接东西两院的长廊拐角时——
声音。
低沉压抑的、男人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喘息声。
还有……女人细碎如丝、带着哭腔和极度满足的呻吟声,被痛苦与欢愉扭曲得断断续续……是从西翼那间特意为小少爷准备的、隔音并不算很好的绘本室传出的!
百合子猛地僵住!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她几乎是本能地想转身逃离,但身体仿佛被无形的恐惧和某种致命的吸引力钉死在了原地!
虚掩的门缝无法窥见全貌,但那被压抑的音浪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她能清晰地想象出那纠缠的身影!是尾形……和阿希莉帕!
在她亲自过问设计、摆满她精心挑选童书的绘本室里!就在儿子的玩具堆旁!
百合子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和头晕目眩。她扶着冰冷的廊柱,身体微微发颤,脸色煞白如纸。屈辱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将她彻底淹没。这声音无休无止,像是在无声地宣告:你看,他在这里,在她和孩子的领域里,如此放肆地与那个女人亲密!毫无顾忌!
那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促,带着一种毁灭般的力量感,最终汇聚成男人一声深埋在喉间的低吼,以及女人高亢到失声的、如同濒死又极度欢愉的短促尖叫后彻底瘫软的呜咽。
接着,是死一样的寂静。
百合子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突然!绘本室的门“唰”地一声被拉开!
百合子猝不及防,几乎和站在门口的人撞个正着!
是尾形!
他穿着墨蓝色的丝绸单衣,领口凌乱敞开,露出棱角分明的锁喉和小片汗湿结实的胸膛。几缕湿润的黑发粘在他轮廓深刻却略显疲惫的额角。他身上的气息混浊而灼热——汗水、情欲、还有……那个女人的气息。
看到突然出现在门外的百合子,尾形那双深潭般的瞳孔骤然缩紧了一下,随即迅速冻结成一片无机质的冰冷。那里面没有一丝被撞破的慌乱或羞耻,只有一种被打扰核心领地的、骤然降下的暴风雪般的寒意。他的目光如同淬毒的冰锥,毫无遮掩地刺向百合子惊惶失措的双眼。
百合子在那样的目光下,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住!她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记了。
尾形没有开口。他只是极其冷漠、甚至带着一丝嫌恶地扫了她一眼,仿佛她是误闯禁地的尘埃。随即,他侧身,毫不停留地从她身边擦肩而过。冰冷坚硬的肩膀甚至撞得她踉跄了一下。他大步离开,方向是后院的浴池,显然需要清洗身上的痕迹。
百合子扶着冰冷的廊柱,才勉强支撑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她的目光下意识地、带着她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怯懦和好奇,投向了虚掩的绘本室门口。
映入眼帘的,让她瞬间凝固。
阿希莉帕躺在一张铺着厚软垫的地毯上,身上只覆着一条被胡乱扯开的、薄薄的浴衣。她的长发散乱如同海藻般铺在身下,脸颊如同抹了最艳的胭脂,布满激情后的红晕,双眼迷离半睁,蓝眸里氤氲着未散的水汽和极致满足后的茫然放空。剧烈起伏的胸膛袒露在空气中,那年轻饱满、形状诱人的双乳顶端,红肿挺立,覆盖着清晰的指痕和……新鲜的紫红瘀痕(吮吸造成的)!她的腰肢以下被揉皱的浴衣覆盖,但一双线条匀称、带着婴儿般细腻质感的白皙大腿暴露在空气中,腿根处能看到明显被大力捏握过的泛红指印……以及星星点点的、未擦干的、属于男人的……暧昧水痕和不明浊液,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
她整个人如同被狂风骤雨彻底摧折后的娇花,破碎、绽放、散发着极度淫靡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情欲的腥膻味。
这一刻,百合子浑身冰冷如堕冰窟!她死死地盯着阿希莉帕锁骨下方一处新鲜的深紫色吻痕——如同一个暴烈的烙印!
紧接着,一股尖锐的、令人窒息的刺痛感从百合子自己空荡荡的胸口猛地炸开!仿佛有无数根冰冷的针在扎!不是情欲……是另一种更绝望的疼痛——
是被彻底忽略、彻底遗忘、甚至视为无物的——没有吻痕的痛!
她像被烫伤般猛地收回视线,捂住突然剧痛起来的胸口(那只是一种神经质的痉挛性反应),转身扶着冰冷的墙壁,几乎是跌跌撞撞地逃离了那个散发着浓烈禁忌气息的地方。每一步都如同踩在刀尖上。
身后,阿希莉帕似乎才从情欲的余波中缓缓回神,发出一声如同幼猫般的嘤咛。
那声音,让百合子逃离的脚步更快了。她没有眼泪,只有一种浑身都暴露在烈日下、却感到刺骨冰寒的巨大羞耻和心口空洞的、针扎般的痛楚在无声蔓延。
一个拥有着一切“正式身份”的正室夫人,像一个见不得光的小偷,落荒而逃。只留下那个被禁忌情欲碾过、身体布满新鲜烙印的年轻女孩,慵懒地躺在狼藉的地毯上,享受着劫后余生般的疲惫与满足。
这就是她的丈夫与他的情人。这就是她——高岭百合子——在花泽家这座冰冷金丝笼里,唯一的“正名”。没有温度,没有气息,更没有……痕迹。
仿佛宿命的嘲弄,又或是这偌大宅邸对她刻意的惩罚。百合子开始像一个被无形丝线牵引的幽灵,一次次在巧合(亦或是潜意识深处的自虐)下,撞见那灼伤灵魂的场景。尾形百之助与明日子之间那惊心动魄的亲密,似乎总能穿透隐秘的缝隙,赤裸裸地呈现于她的眼前。
午后,百合子受父亲之托,亲自去茶室取一套待客用的贵重古窑茶具。茶室位于僻静角落,需穿过一道由高大屏风隔开的窄弄。当她端着装有茶具的沉重红漆描金托盘,小心翼翼转过屏风时——
阳光斜斜地穿透竹帘,在榻榻米上投下斑驳的光斑。
阿希莉帕背对着屏风方向,被压在靠窗的矮几边缘。
她的衣衫半解,松垮的米白色小袖被褪至臂弯,大片光洁无瑕的裸背暴露在阳光里,像一块温润的羊脂白玉。腰肢因被身后的力量迫使得深深下弯,形成一道充满柔韧性的、惊心动魄的弧线。墨蓝色的丝绸(显然是尾形)紧紧覆盖在她身后,贴着她赤裸的腰背曲线向下延伸,被揉乱,堆积在她紧绷饱满的后臀之上。
低沉的喘息声混合着如同幼猫被钳制咽喉般的呜咽从她喉间逸出。百合子甚至看到了矮几边缘那只悬空的、圆润白皙的脚踝,脚趾紧绷蜷缩,无助地在空气中点划。
屏风的另一端,被阴影笼罩,百合子无法看清尾形的脸,却清晰无比地捕捉到了那低沉压抑的闷哼声。
还有……手掌。
一只骨节分明、力量感十足的大手,清晰地从阿希莉帕的颈后缓慢地、充满力道地向下抚摸——掠过蝴蝶骨紧绷的棱角,滑过凹陷的脊柱沟,最终牢牢地盖住了她那挺翘圆润、在光线中凝脂般光滑的后臀。那五根手指甚至带着占有的欲念,微微用力地嵌入了那团饱满软弹的臀肉里,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仿佛在宣告这是不容任何人觊觎的疆土。
百合子的心脏如同被重锤击中!指尖一麻,沉重的托盘连同里面价值连城的古窑茶具,“哗啦——!” 一声,狠狠砸在榻榻米上!青瓷碎裂的声音如同利刃,瞬间割裂了午后茶室的寂静和那道旖旎的声响!
屏风后的动静瞬间停止!如同凝固的火焰。空气凝滞得令人窒息。
几秒钟后,一件墨蓝色的丝绸外袍带着残余的温热和属于尾形的、混着麝香味道的气息,被粗暴地抛过来,精准地砸落在百合子脚边!将一地狼藉和破碎的茶具完全覆盖!无声的驱逐令!
随即,是抱着阿希莉帕(用那件撕裂的米色小袖紧紧裹着)快步离去的沉重脚步声。
百合子呆呆地站在原地,裙裾溅上了冰凉的茶水。她看着脚边那件覆盖了“罪证”的、象征着丈夫气味的外袍,浑身的血液都变得冰冷。那只死死捏攥揉握着阿希莉帕臀峰的大手形状,清晰地烙印在视网膜上,再也无法抹去。羞辱感如硫酸般烧灼着她的五脏六腑。她缓缓蹲下身,不是因为收拾残局,而是身体再也支撑不住那份沉重的冰凉和难言的幻痛——她的后腰背和臀部,从未感受过那样绝对力量的揉捏和占有性按压的地方,竟也在那视觉的刺激下,生出了一阵细微的、痉挛般的、带着强烈渴望却永远无法被满足的空无幻痛。
某个闷热的夏夜,百合子因心绪不宁难以入睡,独自在偏僻的月见台附近透气纳凉。树影幢幢,掩盖着旁边小偏厅虚掩的纸门内未散尽的热气。
压抑的、急促的肉体撞击声混合着水汽弥漫的扑溅声,穿透门扉细微的缝隙,毫无预兆地灌入她的耳朵!
“唔…慢点…太快了…啊!” —— 阿希莉帕带着哭腔的、被过度索取般的短促求饶声被瞬间打断!
“哗啦!哗啦啦啦——!” 剧烈的水花泼溅声骤然响起!像是有沉重的身体被凶狠地压入了浴桶之中,水面激烈地拍打着桶壁!
尾形低沉沙哑、如同困兽喘息的声音随即传来,带着一种近乎狂野的压迫力和不满足的焦躁:
“…这就受不了了?刚才…是谁缠着要在这里的?…嗯?!”
撞击声更加密集疯狂!“啪!啪!啪!”肉体拍击水面的声音伴随着更加破碎绝望的呜咽和被迫承受的水下窒息的“咕噜”声此起彼伏!
百合子死死地捂住耳朵,却无法隔绝那可怕的、几乎要撞破胸膛的律动声和阿希莉帕那被强行堵回喉咙深处的、痛苦与快感交织的濒死呜咽!她仿佛能看见那个年轻的女孩被丈夫按着头压制在温热的浴桶里,水灌入口鼻,丰腴的大腿被迫高高举起跨在桶沿,臀瓣因为身后猛烈的撞击而在水波中剧烈晃荡颤抖……水面不断被沉重的冲撞激起巨大的涟漪和水花!
强烈的窒息感和令人作呕的生理不适席卷了百合子!她扶着冰冷的墙壁剧烈地干呕起来,胃部痉挛成一团。那只强按着阿希莉帕头颅、将她在浴桶水浪里狠戾贯冲的无形大手,隔着冰冷的墙壁,似乎也扼住了百合子的喉咙!她自己的后颈和后脑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力量压制下的空无钝痛!那份屈辱感和被强力支配的恐惧感,如寒潮般将她彻底冻结!
她几乎是连滚爬爬地逃离了那个角落,逃离了那水声混合着绝望呜咽的声浪。当晚,她发起了高烧,在昏沉中,那浴桶中的窒息感与被无形之手按压的幻痛反复折磨着她。
百合子卧病期间,侍女们在茶水间的议论更是肆无忌惮。
“啧啧,你是没看见那套茶具!高岭夫人娘家送的古董呢!说是夫人失手打了……”
“我看未必是失手……”
“怎么说?”
“你想啊,先生从那茶室出来的时候……啧啧,明日子夫人被抱着,那件罩衣底下啥也没穿吧?后来听菊子姐说,在茶室里面……明日子夫人的后臀上……全是红红的手印子!”
“天哪!先生这么……有劲?”(语气带着惊恐又有一丝隐秘的向往)
“是啊!听说都……捏进肉里了!夫人正撞上呢!你说她能不气吗?砸了东西也不稀奇……”
“唉,可怜……先生看都没看她一眼吧?抱着明日子夫人就走了。那件盖碎片的衣服也是先生的。”
“啧啧……”
(压低声音)“你说……高岭夫人……是不是这儿……”(用指尖轻轻点了点太阳穴,暗示疯了)“……受不了?”
“嘘——!别胡说!”
百合子病愈后,在廊下短暂经过时,听到两个负责清理庭院的老园丁聊天:
“……昨晚月见台那边偏厅的动静听见没?闹腾得……”
“听见了!哎哟,那水泼得……跟打仗似的!”
“先生真是……兴致好……”
“明日子夫人年纪轻……又生得那副样子(压低声音,语气带某种低俗的臆想)……先生能不爱往死里折腾吗?”
“也是……跟个活生生的洋娃娃似的……”
老园丁吐了口烟,“洋娃娃?嘿……我看先生那劲儿,更像是逮着了什么山精妖怪……要拆吞入腹才肯罢休咧!”
“山精?……呵,北地来的蛮女……”
两人心照不宣地怪笑起来。
这些粗鄙的、带着臆想和恶意的议论,如同细密的毒针,日复一日地扎在百合子千疮百孔的神经上。她成了佣人口中或明或暗的谈资:一个撞见丈夫与情妇狎昵而情绪崩溃的“疯女人”,一个失手砸碎珍贵古董的笨手笨脚的失宠夫人,一个永远无法被丈夫狂暴而专注的情欲所触碰的透明人。
每一次“目睹”,都是对她存在感的又一次凌迟。每一次议论,都像将她心底那份幻痛撕开,摊在众目睽睽之下任人嘲弄。
那只在阿希莉帕赤裸身体上留下清晰指印、在水中掀起狂澜的手,从未降临百合子哪怕分毫。
可那每一次旁观,那每一次听闻,那每一次关于阿希莉帕如何在丈夫身下辗转承欢、如何被揉捏细节描述……都在百合子从未被触碰过的腰臀曲线、后颈皮肤上,刻下了一道道只有她自己能感受到的、冰冷而鲜活的空无指痕,带来一阵阵永无止境的、名为“未存在却渴望被烙印之痛”的幻肢痛感。
她依旧精致、优雅、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花泽夫人的职责。但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华服之下,那具年轻而充满生命力的身体,已然成为了最冰冷、最空虚的牢笼。她在丈夫眼中是空气。在众人眼中,是一场盛大而悲凉的陪衬。而对丈夫与明日子夫人那如同禁忌图腾般的纠缠,她永远是那个被隔绝在祭坛之外、只能遥遥窥见一丝血光与湿热的旁观祭品。疼痛,在她未被触碰的肌肤上无声地生长、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