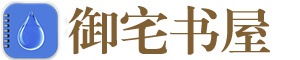避难所
作品:《情迷1942(二战德国)》 男人的动作顿住了,他回过头去。
俞琬站在楼梯的阴影里,肩膀微微发抖,外面的火光斜斜打过来,照见睫毛上挂着的泪珠,不知是真是假,但闪着细碎的光。
“那里……不能进去。”她的声音很轻,每个字都像耗费了很大力气,“晚上爆炸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就躲到那里面去了……”
她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带着近乎赤裸地哀求,像只受惊后躲进洞穴,又被强行揪出来的兔子。
“里面……有我的睡衣,还有……一些私人的东西。很乱……”女孩断断续续地说。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那声音几乎消失了,仿佛仅仅是描述那个“乱”的景象,就足以让她想把自己埋起来。
君舍静静看着她,看了很久,这个平日里总是温婉从容的小女人,此刻窘迫得几乎要哭出来,就因为自己的“秘密小窝”即将被入侵?
呵,受惊的小兔,叼着最珍视的胡萝卜和最柔软的草料,慌不择路地钻进地洞,天真地以为那里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这荒谬的联想,竟让他嘴角不受控地扬了一下。
“私人的东西?”男人开口,重新染上那种惯有的慵懒腔调,“比如……克莱恩送你的小礼物?”
看啊,奥托,当你的同僚正在街垒后浴血奋战时,你却站在这里,站在你昔日同窗未婚妻的“避难所”门前,带着病态的窥私欲,还有闲情逸致开这种不入流的玩笑。
俞琬狠狠咬了咬嘴唇,用疼痛逼自己清醒些,再开口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唧:“克莱恩说……地下室只有我和他能进,他说……那里是我的安全屋。”
他既然主动提到克莱恩,那就干脆把克莱恩搬出来。
想到这,她把“克莱恩”这个名字咬得格外重些,像是在两人之间竖起一道无形的界碑。
君舍的眸光暗了暗,有什么东西像被惊动的深潭水藻,缓缓沉了下去。
俞琬的睫毛颤了颤,眼泪真的不堪重负掉下来了,七分是实打实的怕,只有三分是演出来的。
有那么一瞬间,她也几乎以为他要硬闯了,因为他眼底刚才一闪而过的东西,太像野兽嗅到血腥味时的兴奋模样了。
“看来我这位老伙计,连个地下室都要划地盘。”男人轻笑一声,忽然松开了门把手。
“抱歉。”他退后一步,那种玩世不恭的笑容又像面具严丝合缝回到脸上去,“是我冒昧了,我老伙计说得对,女士的私密空间,确实不该擅闯。”
“我大概是……”君舍顿了顿,嘴角勾起自嘲的弧度来。“是太‘费心’了,克莱恩在前线拼命,却留您一个人在变成火海的巴黎…既然有所托付,总得替他多看两眼,是不是?”
男人不再看她,转身走到窗边,指尖挑起窗帘一角,刹那间,窗外的火光涌了进来,将他半边侧脸映成橘红色,另外半边,则彻底沉入晦暗中去。
“巴黎在开一场不太优雅的派对。”
君舍对着那道缝隙轻声说,像在评论一出与他无关的荒诞剧,“不过别担心,你这里很安全,我的人,会守到最后一颗子弹。”
他放下窗帘,隔绝了最后一点摇曳的火光,踱步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却迟迟没有拧开。
男人忍不住回头,又看了女孩一眼,苍白的脸,微红的眼眶,起了球的针织外套格外单薄,还有那双绞在一起的纤细手指,指尖都泛着白。
这小兔,被吓着了。
“明天的火车…照常开,北站还在我们控制下。”他顿了顿,语调竟奇异地放柔了些:“但我会亲自来接你,八点整,我带小女士穿过战区去车站。”
俞琬的呼吸都要被扼住了。
他要亲自来接……到时候从这扇门到火车站,她的每一步都会在他眼皮子底下了。
但她强迫自己点头,声音发颤:“谢谢您,上校。”
“到了柏林……”君舍忽然话锋一转,语气像是在闲聊,“小女士可以重新开个诊所。比这儿大,安静,没人打扰。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有栋房子,很合适。”
这是明晃晃用“柏林的新生活”当胡萝卜,吊在这只受惊的小兔眼前。
俞琬低下头,盯着自己绞紧的手指,一言不发。她不想接话,也不知道该怎么接。
男人笑了笑,倒也不在意,却又在拉开门前,侧过头似笑非笑睨了她一眼。
“好好休息,”声音带着关切,却让女孩后背发凉。“明天…会很漫长。”
门关上了,落锁的声音很轻,却重重砸在心上。
约翰…你在哪里……
时间像是被拉长的橡皮筋,每一秒都缓慢得让人呼吸发紧。
俞琬没有力气再站着,便顺着楼梯滑坐下来,将自己蜷缩成一团,耳朵却竖起来,拼命捕捉着外面每一个声响,每一次爆炸,每一次枪响,每一次脚步声。
约翰会不会……不,不会的,她用力摇头,他那么厉害,是克莱恩手下最好的兵,可那念头还是像毒蛇一样,死死缠在心头,他只是去探探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炮弹无眼,他会不会受伤倒在某个巷子里,流干了血,直到天亮也没人发现……
天色开始翻起鱼肚白的时候,外面的枪声稀疏了一些。但随即而来的是更沉重的爆炸声,是起义军在炸街垒。
一个士兵进来检查窗户,看见俞琬还坐在楼梯上,不由得愣了愣。
“女士,您该休息了。”他生硬地说,“这里很安全。”
女孩机械地点了点头,身体却没有动。她怎么睡得着?越等心越慌,还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干,她扶着墙壁站起身,腿脚发麻,却还是强撑着煮了一小壶黑咖啡。
她给门口每一个士兵都倒了一杯。
“谢谢,女士。”一个士兵轻声道谢,他的指关节已然冻得发红,“您……还好吗?”
俞琬轻轻摇了摇头,又茫然点了点头,最后只是挤出一句:“还活着。”
约翰还没有回来。
枪声像是永不停歇的背景音。女孩缩回原来的地方,每一次后院有动静,她的心都会猛地提起来,绷紧了神经去听,又悻悻落回去。
绝望在一寸寸滋长,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惫压得她有些撑不住,迷迷糊糊间,女孩打起了盹。梦里全是破碎的画面:克莱恩在坦克舱口朝她挥手,君舍站在燃烧的巴黎街头对她笑,约翰浑身是血地倒在巷子里……
咚、咚——咚
她是被一种有节奏的敲击声惊醒的。
地窖门板传来的声音,两短一长,正是约翰的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