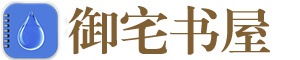鬓边待诏 第77节
作品:《鬓边待诏》 但心里仍是暗暗喜欢的,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有人亲手给她做花灯。
灯市的烛光从阁楼下漫上来,月上中天,洒下一片银辉如雾。谢及音靠在裴望初肩头,耳边听着楼下的喧嚣声,看着他将一圈圈竹条搭成一个球,错镂相接,像一个漂亮的笼子。
“巽之。”
“困了吗?”裴望初侧过脸来看她。
谢及音摇了摇头。只是瞧他生得好看,又那么专注,故意要打搅他。
蜡烛搁在竹筒做的蜡台里,悬在竹笼中央,他扯过红纸,用鱼胶小心糊在竹笼之外,然后以黑炭作笔,在纸上画了几朵简笔勾勒的桃花。
这就算做好了,裴望初将花灯递给她。谢及音疑惑道:“没有提杆,这要怎么拿?”
裴望初道:“不必提着,抱在怀里即可。”
谢及音怕里面的蜡烛翻倒灼伤她,裴望初却握着她的手,将那花灯往地上一推,让它滚远了。
“小心!”谢及音吓了一跳,担心蜡烛将花灯点燃,却见那花灯滚了两圈后,安然无恙地停下,里头的蜡烛也没有倾倒,映得红纸上的桃花灼灼正盛。
谢及音十分惊讶,好奇地将它捡起来,仔细打量,发现大竹笼里套着小竹笼,衔接处是活的,不知用了什么机窍,无论怎么翻滚,里面的蜡烛始终朝上。
“这是从天授宫的典籍里学来的,名字叫‘长生灯’,取其长生不灭之意。”
“长生灯……此物倒是奇巧。”
谢及音将花灯抱在手中来回翻动,从缝隙里觑里面的蜡烛如何保持朝上的姿态。
烛光映着她的眉眼,月辉洒在她发间,像天上的仙姝好奇人间的热闹,偷偷溜下云间,嗔时如花隔云端,笑时又亲切宜人,叫人怀疑拿一盏花灯就能骗走。
她抱着那长生灯爱不释手,说道:“我要好好留着,等卿凰大一些,她一定喜欢这个。”
卿凰刚生下来裴望初就走了,连她的满月也没赶上,也不怪她不认得自己。今夜听见她的哭声比刚出生那天更有力,看来被养得很壮实。
他自身后拥住谢及音,为她挡下身后吹来的风,温声道:“我是该早些回来,卿凰这段日子是不是吵着你了?”
谢及音笑着叹气,“你不知道她有多能闹,整座显阳宫,谁也别想清净。我幼时可是很安静的,你说她这是像谁,嗯?”
裴望初也不认,怕她以后牵连自己,“说不定殿下幼时本该与卿凰一样,只是被压抑了天性。”
谢及音轻哼,觉得他在瞎说,她天生就是这样温和柔善。
“以后我来带卿凰,再不让她吵着你。”裴望初道。
第86章 作画
禁军奉陛下口谕, 将郑君容置在昌南坊的宅子给查封了。
那里面还关着骆怀盈,郑君容得知此事后,急匆匆去见裴望初。他当然知道师兄是记仇他在皇后面前背刺他的事, 但仍替自己辩白道:“袁崇礼的孙女确实善酿屠苏酒,你也确实往胶东去了,我句句都是实言,皇后娘娘多心,不正是师兄想要的故弄玄虚之效吗?如今为何又来寻我的碴?”
“我也没说怪你, 凡事都与皇后说, 你做得很对,”裴望初笑得春风和煦, “那你以后就继续这样干。”
郑君容躬身:“再不敢了。”
裴望初慢悠悠说道:“听说有人在你那宅子附近丢了一头牛, 事关盗窃,朕让禁军去看看也是应该,反正你平时又不住那宅子。”
“那宅子里……”
“怎么,见不得人?”
郑君容在他似笑非笑的眼神里哑了声, 羞窘得双耳通红。
骆怀盈是宫中放出去的后妃, 她的身份确实见不得光,又是被他强行关在那宅子里, 在这件事上, 无论对谁,郑君容都是理亏的。
“宅子里的人你不必担心, 但是三个月内,不许你再踏足那宅子。”
裴望初点了点堆在案头那摞已经批复完的折子,吩咐他道:“并非蔡氏倒了就万事大吉, 改税是在割世家的肉,有些人还想闹幺蛾子, 你要派钦天监的人盯紧。还有请袁崇礼出任太学五经博士一事,也交给你去安排。”
突然领了一堆冗事,刚处置完蔡氏后事打算歇口气的郑君容深深叹了口气,“臣遵命。”
收拾完郑君容,接着便是王瞻。
但王瞻比较棘手,他将人家从建康请来勤王,既有苦劳也有功劳,更兼与皇后有君子之交,他若是去为难王瞻,显得太没肚量。
但是看着至今仍挂在显阳宫的那盏出自王瞻之手的花灯,裴望初觉得若是不为难他,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思前想后,他将王旬晖叫来,闲叙间聊到了王瞻的婚事。
体恤臣下的永嘉帝态度亲切:“子昂长朕一岁,如今朕已有妻女在侧,子昂却仍孤身一人,朕瞧着实不忍心。他父亲亡故,母亲不理事,你是他的堂叔,该替他上点心。”
王旬晖何尝不想让王瞻成婚,只是给他相看过很多女郎,他总有不中意的借口。今日闻得天子此言,王旬晖如开闸放洪,跪在地上大倒了一通苦水。
裴望初听得直皱眉,“子昂他竟如此不想成婚?”
事关他的皇后,他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揣摩一个君子,他不由得深思,王瞻是在为谁抗拒成婚,心里又怀着什么希望。
纵他不争不抢,可他毕竟摆出了一副窥伺的姿态。
王瞻态度坚定,裴望初的态度可以更坚定。
他敲打王旬晖道:“无父母妻女是无挂碍,若你是朕,敢将兵权交在这样的人手里吗?”
王旬晖一听此言,瞬间背冒冷汗。
他急忙跪在地上表忠心,裴望初不耐烦听这些,只说道:“你回去劝劝子昂,叫他先立身齐家,否则就算朕不与他计较,御史台早晚也会参他。”
“臣遵旨,这次一定好好劝他。”王旬晖战战兢兢地领下此命。
过了几日,王瞻前来觐见,裴望初避开了显阳宫,在宣室殿里摆了一枰棋,邀王瞻上前对弈。
王瞻却收了棋盘上的棋子,逐一放回棋篓中,并没有与他手谈的意思。
他开门见山地对裴望初说道:“我知你在担忧什么,你放心,我不会与你争抢。但我不争抢,是因为深知她不会动摇,并非因为你是帝王,所以也请你不要以帝王的身份压我,逼我做并不情愿的事。”
闻言,裴望初也将掌中棋子扔回篓中,“如此说来,倒是我以俗心观人,看矮了子昂兄。”
王瞻本想说,易地而处他也会有这种担忧,又怕此话会让他更生猜疑,遂并未说出口。他说道:“能于波谲云诡的朝局中护她一回,我已十分感激。”
裴望初不言,内侍奉上茶来,两人换了话题,聊了些朝政上的琐事和建康的风物,后来又不知如何聊回了许多年前的事。
那时魏灵帝尚在朝,裴望初自胶东袁氏学成归来,迅速在洛阳声名大噪。
“我以为你同我一样,是世家培养的一具傀儡,是推给世人看的门面,直到你入了公主府,我才发现并非如此,若是王家落到那个地步,我绝没有勇气在世人的指摘中活下去。你所看轻的东西、所看重的东西,似乎都与我们不同,你既非君子,也非小人。”
裴望初闻言笑了笑:“那我是什么人?”
王瞻说:“我不知道。”
裴望初自言自语道:“我大概是……求她的人。”
那盏挂在显阳宫的花灯,最终以怕被雨淋坏的借口收了起来,裴望初命人收进了内库深处,与谢及音说要亲自画一盏挂上。
他的丹青虽不如王瞻驰名,但功力并不浅,至少在谢及音品鉴过的画作中称得上数一数二。
谢及音旁观他在灯纸上画桃花,问道:“你怕子昂送的花灯淋了雨,难道就不可惜自己的花灯吗?”
“淋坏了就画新的,”裴望初提笔道,“反正我就在这儿,只要殿下喜欢,夜夜如新也未尝不可。”
“可是每一幅画毕竟不同,这副桃花我就很喜欢。”
谢及音抽过那宣纸仔细端详,觉得这花枝很像他曾为她簪发的那一枝,越看越喜欢,“倒不如挂在廊下,有回廊遮着,也能少受几分风雨。”
“你若是喜欢这个……”
裴望初自身后揽住她,侧首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谢及音的耳朵一红,像是宣纸上的桃花被风吹起,渐渐晕染上双颊。
“允我一回,行不行?”裴望初在她耳边低声问。
谢及音并非不心动,只是什么花样,允了他一回,此后必有第二回第三回。
那凭几上的云纹已快要被她汗淋淋的掌心磨平,金铃系在脚踝上,也隐隐有了绳痕,更别说那金绡帐中她数次攀扶的床头狮兽雕……
越想心越乱,谢及音拾起团扇半遮住面,觑他仍要来缠,搁下那画纸,施施然起身走了。
入夜时分,画好的宫灯已挂在了廊下,金绡帐里也点着灯,照出脂莹如粉堆,玉白如冰砌。
描眉的螺黛为墨,自yao际探出一支桃枝,上至蝴蝶骨,下至腿/心。用捣碎的花汁描成桃花灼灼,粉/瓣簌簌,又以朱砂点蕊,析汗为露。
画好之后,裴望初从妆台上取来铜镜,照给她看。
虽然作画的过程免不了嬉闹,但画成这一树桃花,却只见风流写意,不显丝毫狎昵情态。谢及音很喜欢,对着镜子照了许久,而后敛羞朝裴望初转身,叫他在前面也画一支。
裴望初靠在床头,帐中宫灯照得他眉目如水,缓缓自她身上淌过。
他手中捏着螺黛,俯身贴近她,低声在她耳边道:“你这样遮着叫我怎么办……要把头发撩到后面去。”
作画人的手沿着画纸一寸寸抚平、轻揉,要使它足够柔软平滑,才能吸住颜料。这其中必然夹杂私情,有几回越了界,险些打翻那红艳的花汁。
桃花开在金绡帐里,被风一吹,颤颤不息。
闹到夜深,第二天必然醒得晚。幸好裴望初念她脸皮薄,早已将东西收拾干净,又亲自侍奉她更衣洗漱,未假手于人。
在妆台为她绾发时,见她神思恹恹,裴望初道:“今日这么困乏,吃过饭再睡一会儿吧。”
谢及音轻轻摇头,“召了几位世家夫人,等会儿要去见见。”
她将画花钿的朱砂笔拿给他,微微朝他仰面:“想要红莲花钿,能画么?”
识玉进来通禀时,裴望初正画完最后一笔,又从妆匣里挑了一支镂金莲花钗,推进她发间。
“皇后娘娘今日姿容照人,凡事不必委屈自己。”
“知道了。”趁识玉转身的功夫,谢及音突然仰面亲了他一下,将梅子色的口脂印在他唇间。
裴望初抿唇,含笑将目光落向一旁。
谢及音今日要见的是洛阳城里几大世家的掌家夫人,这些世家一向关系紧密,当初与陈留蔡氏也往来甚多。蔡氏倒后,他们纷纷落井下石,想要撇清关系。
然而世代姻亲、年来节往,这藕断丝连的关系是没那么容易甩干净的。
几位夫人请安毕,谢及音让识玉将蔡氏嫡女蔡锦怡请出来,与各位夫人见礼。
夫人们见了她,皆脸色微变,恨不能装作不认识,却又不得不与她礼节周全。谢及音似是没注意到她们的局促,正端着茶盏,以茶汤为镜,悄悄欣赏画在额间的红莲花钿。
画得真美,以后要多挑些花样,日日都画。
“听锦怡说,从前几位夫人与蔡氏多有来往,如今蔡氏落得这个下场,不知各位作何感想?”谢及音慢条斯理地问道。
赵夫人笑得有些牵强:“皇后娘娘可能有所误会,我们与蔡氏只是寻常往来,纵为姻亲,也并非同气相连。蔡氏落得如今下场,乃是违背国法、为祸乡里之故,与我等实在不相干。”
谢及音朝识玉点点头,识玉向几位夫人呈上一张长长的礼单,上面详细记录了蔡氏与这几位世家的利益往来。
赵夫人脸色唰然一白,瞪向蔡锦怡:“锦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