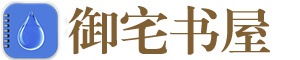28、冷羿
作品:《蝴蝶与恶魔[校园]》 十二岁那年暑假,冷羿攀岩摔断腿,落地的时候膝盖咔咔两声,挺疼的。
温女士难得心疼了他一回,每天各种补汤往病房送,跟他讲话也轻声细语,那是冷羿头一次发觉他妈是个温柔的女人,并且觉得这回受伤是个好事儿。
腿伤了,不用陪温女士满世界到处飞,出院后冷羿闷在房间打了两天游戏,第三天温女士打来一通国际长途告诉他明天家教上门,叫他收心准备上课。
真服了。
冷羿在电话里一言不发,十二岁他个子窜高,那根叛逆骨头也蹭蹭长,连夜收拾东西坐车去爷爷家。
他爷爷是个有趣的老头,奶奶过世后他一个人搬回了老房子,别人回乡下都是种花种菜,他特立独行,收养一屋子流浪猫狗,其中有只土不土洋不洋的黑狗,他爷爷管它叫小羿。
冷羿当时挺无语,后来知道他爸他妈甚至他伯叔堂哥的名儿都有对应的猫狗心里头才舒坦了。
在小镇上待了几天,哪怕足不出户也不觉得无聊,每天逗逗猫玩玩狗,听爷爷唱唱小曲儿,日子舒服得忘乎所以。
可温女士就见不得他舒服,即使隔着四大洋五大洲她也能想办法塞一个人形监视器过来,视奸他的一举一动。
说视奸当然是夸张了,而且那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心智好像只有三岁,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且十分热衷于一些低级趣味。有两天他经常往冷羿房间跑,拿一台手持望远镜站在窗口望,冷羿一看他那贼眉鼠眼的样子就知道他没干好事,朝他后背砸一个枕头问他在看什么,冷煦回头看他,眼睛眯得像个地痞流氓,说隔壁住着一个超好看的妞儿。
哦,搞半天是在偷窥。
那个年纪正是性别意识觉醒的时期,对异性产生好奇心和探索欲是件很正常的事,因此冷羿没有出言嘲讽他这素质低下的堂哥,只是对他的猥琐行为投去一个鄙视眼神。
过后冷煦这缺心眼继续一天到晚粘在窗口观望,彻底将“视奸”对象从冷羿换成隔壁的女孩儿。
对面随便做点什么他都一脸春心荡漾,就是出口气他都恨不得自己有双顺风耳,这种在冷羿看来等同发情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某天冷煦再也按捺不住,决定把苦思冥想一晚上的搭讪战术付诸行动。他在后院对着那些猫狗挑挑选选的时候,冷羿用膝盖都能猜到他要搞些什么名堂,他控着轮椅滑过去,指了指那只白毛幼猫,冷煦领悟力不差,咧开嘴冲他比个大拇指,抱着那猫出了门。
冷煦靠着流浪猫成功跟那女孩儿搭上话,只可惜好景不长,隔天人家就怒气冲天跑来用篮球砸碎他家客厅的玻璃门。
冷羿没兴趣关心冷煦干了什么蠢事,他只是看着碎了一地的玻璃。
心想,这姑娘挺烈。
脾气跟乔染不相上下,他觉得这姑娘能处,处成兄弟的那种处,不过她又比乔染机灵一点,一屋子大小因她的惊人举动发懵的时候,她先发制人开始掉眼泪,那种哭是无声的,却极具杀伤力,他亲眼见证爷爷脸上的神情从惊到怒再到怜,整个过程不足五秒,第六秒不留情面地拎起冷煦脖子,拽他过去跟人赔礼道歉。
按理说闹完这一趟冷煦该消停了,但他那个舔狗属性似乎是打娘胎里来的,郁闷没两天又开始粘在冷羿房间的窗口,眼巴巴盯着对面还不够,还要举着手机用音乐软件识别对面正在播的歌。
冷羿已经不想用正常思维去理解他堂哥的反人类行为,在冷煦半个身子摊在外面急得跟热锅上蚂蚁的时候,他靠着床头,慢条斯理地打开音乐播放器,添加进一首英文歌。
那首在女孩房间回旋的情歌留在他的歌单里,被他听了整整五年。
说起来挺玄妙,砸玻璃的事情过后冷羿时常想起那个女孩,那副咬着唇、眼圈通红、肩膀一颤一颤的可怜神态,在他的脑海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美感,一些完全相悖的名词随之聚集到一起,汇成她的阴暗与明亮、腐烂与新鲜、邪恶与纯真。
矛盾,又有趣。
但他没有把这种感觉定义为喜欢,毕竟它实在缥缈,又单调苍白,它更像是一截错了位的骨头,长在不该长的位置,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或情景,产生让这具身躯难以忽视的痛痒。
这种痛痒在那个暑假后数度发作,他在一个暴雨前夕的闷热深夜,意识到自己跟冷煦一样到了对异性产生探索欲的阶段,他无法判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唯有遵从内心,在下个暑假再次去到那个小镇。
然而已经人去楼空。
他问爷爷那户人家去了哪里,爷爷仍旧专注于那些猫猫狗狗,对与自身无关的事毫不关心,只说了句“姓季的那户人?”,然后摆摆手,说不知道。
爷爷说那家人姓季,于是他以为她姓季。
这个误会存在了五年,直到他重新遇到她。
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冷羿再次亲眼见证她拿东西砸碎人家的玻璃。当时他刚跟朋友打完球,经过某幢别墅前听到轰地一声,循声回头时看到一个纤瘦侧影,那天气温降至10度以下,她穿件单薄的卫衣,裸露在外的手和脖子冻得发红,玻璃爆裂坠地的一瞬她的眼眶也变得通红。
冷羿依旧没兴趣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他看着女孩在风中瑟瑟发抖的窘迫模样。
心想,这姑娘挺惨。
跟这户人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冷羿记得这家好像姓鹿,搬进来没多久,他家女儿往他家送过一次蛋糕,他见过,姑娘模样长得挺灵,眉眼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不过那时他没多琢磨,只觉得容貌姣好的女孩好看的地方都差不多,直至在此刻遇上眼前的她,那个尘封在记忆里的独特存在,才恍然得知那份熟悉感究竟从何而来。
是她了。
就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