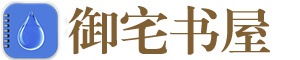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后>笼
作品:《陋篇(古言,NP)》 后梁有一位皇帝,两位坐龙椅的人。
正位去忙,假位的就来了。
他穿行爪牙,登三阶,坐进屏风:“我替皇兄几天。”
我替皇兄,他总是这么说,说话时,轻咬字,没有什么气息;日常的穿戴也特别,有时前角后纱,有时白发垂肩,更多时候被体深邃,像一具彩色的壳。
新的宫人见了他,以为是俑人,都佩服天家大匠好造物,等他“替皇兄”地开口,才受惊,不敢再看。
不过,省中上下,小到一掌故,大到万户侯,没人稀奇他。年轻的宫人就不解了——正朔改变以后,这些小孩才懂事,不知上一代的苦乐与追求——他们远随幽灵一样的白发人:“他是谁呢。”
宾连出面斥责:“议论上人,毫不知耻!”
她驱散宫人,不许他们说闲话,自己去追,追上那头白发,便改为趋步,目送其走进名为“肖筑堂”的宫室,才松口气,心里生出一种满足。
姓茅的大宫令告诉宾连:“小女宾连,由你照顾贵人。”宾连受命,给家里寄信,一笔一画地写:“女儿无印、无章,被茅大人委以重任,照顾一位白发上人。上人真美。”
上人真美,像月色在天。宾连出身烂漫扶风,是一户商人的长女,秀木一样成长,入宫到今天,心始终康健,所以出口成颂。
她不知那位白发贵人爱听颂否,姑且对着他的后背说了,却得到一次对视:他转头,弯眉毛,衔白发,好像在笑,两眼却空,看宾连,把她的冷汗都看下来。
再寄信时,宾连咬牙:“上人真美,然而有哀情,女儿想弄清楚,奈何身为宫官。唉唉。”
最近的一次国朝战争,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如今欣欣世界,什么都好,省中不再是某家窟穴,而是高台,能攀登者能参星拜月,如宾连这样的家庭,也愿意把女儿送去:“我们这位皇帝,在赵国则封二位女子侯,在省则收士伍,以经博士授平民,眼界不同于历代,很了不起。况且我扶风有名望才子,在朝为相。啧,我土高过他处土,所以宾连,你去努努力。”
宾连怀揣一抷乡土来了,两眼都是热情,看什么都好,除了白发间的眼睛。
那次以后,宾连再不敢在他背后说好话,只是默默地跟着,同时与众人做一样的猜测:他是谁呢。
他是谁?他不就是……
一名观星待诏险些说漏嘴,被另一名点了,急忙收住。
观星待诏供职天数台,听讲于国师,在过去,为了革洗旧世代,吃过一次大苦,所以当朝地位很高。哪怕宾连急切想听,也不能逾越,去追问他们什么,只好竖耳在旁,好歹听到一些:
“龙。”
“聋。”
“隆。”
是什么呢?过后,宾连独自穿行宫台,想着想着,豁然笑了:“能坐省中主位,不是龙是什么。”
恰好正位归省,仪仗凌人。
宾连拜在道旁,将苦恼藏进身的阴影里:“不是龙吧,不然这位又是谁。”
人马走远,她继续想,觉得更不是聋,便把隆当作正解。
“不是龙,也是凤,总之是隆盛的贵人,不然怎么坐在高处?听说他还称正位的陛下为兄呢。”回到住所,宾连一顿好说宫人,同时说服自己:贵不可言的人,有哀情,或许只是死了爱猫,如此上人,轮不到自己担心,就按茅大人的话,照顾好了。于是饭后,宾连匆匆赶去肖筑堂。
他已经出来了,白发飏飏,向路的一侧、浅水处去。
“啊,这处失修,请走西路。”宾连去他前面引路。
他给宾连一个笑,木头似的。宾连已经很高兴了,趋步在他身后,同时回望肖筑堂。
省中少有旧宫室,这处旧得不行:正殿多次修补,最近一年没什么人管,就不整齐了;池水更差,不但失修,还淤堵,引水出水,连累其他池,总要人疏通。
听说这宫室原来住着一位肖大人,是皇帝的心腹,如今已经当上太傅。宾连是完全不信的,每听到这一说,就问太傅为何离省,太傅为何远赴楚国。
只有一次,她与人争执,声音大了,让白发人侧目。宾连注意到,以为犯错。
“在宫越久,越松懈。”当下,她边走边反省,把人送回住处以后,决心要改,还拜托要好的女侍史写几条简,方便夜读。夜里她念规戒,十分头昏,被冷风一吹,想起一件事。
“又犯错了。”宾连匆匆跑。
她没换宫帐,担心上人受凉,于是夜里去一趟。
掌夜的女子像蛾,围着上人寝殿。
“我来换宫帐。”“去。”
她们拖帨行走,没听宾连说的是什么,就放行了。
宾连狐疑,又是第一次进殿,每一步都很小心,到了阶下,她说打扰:“我换帐。”回应是灯火燎油声。借着灯,宾连看室内,心惊肉跳:“谁拿三人成虎图作壁画呢?”一室绘制的都是恶兆、灾害、奸人,将要脱出墙壁,向室中的铁笼去。
“笼?”宾连以为是布景,与笼子里的人对视。
由于太熟悉,她叫了一声。
掌夜的女子还在走。宾连挽帐出逃,左右冲突,不敢看她们,之后变得不会说笑,只会说笼;半月过去,她自请为夜者,也拖着帨,殿外游行。
相好的女侍史摇头,告诉大官令:“宾连病了,看明亮处就流泪,看好物就阖眼,应该是眩目的病吧,请茅大人放个假,带她医治,不然她一辈子做夜者。”大官令派人去问。宾连谢绝了。
这是省中一件小事,很快无人在意。同样无人在意的还有白发贵人。皇帝回来,他不用“替”,可以休息了,一休息,少有人问候,于是静卧在笼子边上,数着朔望日,身侧堆虫尸,好一段时间被人忘记……最不为人在意的某天,拜访者来了。
夜半,来人把虫尸踏成灰,拜在笼前:“楚王殿下。”
楚王如同复魄,携他的手交谈。
三人成虎壁下,两条长影在动,余处有回声。
“不急于一时。”
“殿下保重。”
“放心,我学了很多,俛首时俛首,顺从时低头。”楚王虽然笑着,目光中却有恨,戚戚的情绪,在容颜与白发当中;如果是故人,熟知云梦与明月,再看如今的他,一定辛酸。好在来人不是,点一点头就要走。
“进退小心。”两人分别。
楚王倚着笼子,复为一具壳;而去者转身,俨然是个朝官,长冠玉佩,正步入省,叫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与楚王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