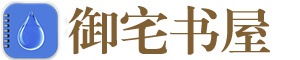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20节
作品:《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强奸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蔡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部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说杨广试图强奸隋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诀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意思是: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就这么死了。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隋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真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些罪名不过是个开始,在这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则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像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不停地宣淫。除此之外,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首先,新皇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所有谥号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人”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他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的地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说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所以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残酷。据《隋书·刑法志》,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第一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 《隋书·刑法志》载,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比起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赋,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继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赋。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隋书·炀帝纪》则记载,杨广继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
因初政的这些举措,杨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隋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载:“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对大隋臣民来说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隋书·炀帝纪》载,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隋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多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处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魏征的《十思疏》。“改革”、“兴作”,这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隋文帝时期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富,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藩王虽然权力也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继位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的。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地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对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都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绝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据袁刚《隋炀帝传》记载,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的人,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斗拔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招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他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外一些可怕的词汇——“不安分”、“破坏性”、“颠覆”——紧密相联。
十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所以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有着毫不讳言的热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清世宗实录》卷七五中记载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自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道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点。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贵族公子的气息。
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看来,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绝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这位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工作的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儿,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隋书·食货志》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中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十七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继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载,这一年,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雄伟壮观。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荫,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贯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据袁刚《隋炀帝传》,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有过如此辉煌的功绩,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尽管杨广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890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4603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十八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如《新唐书·列传第四下》中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的历史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