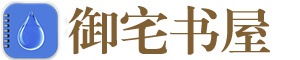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
作品:《1942》 chapter.31
「莫居凡,我想你了。」
莫居凡沉默了,他有点,受宠若惊?或许这也是他意料之内的事情。
温时宇把话筒紧紧贴在耳边,电话那头十分的安静,他怕了,他终于知道怕了。莫居凡之前掛了他那么多次电话他都不怕,可是现在电话通了,他要说的说完了,他怕了。
隔着电话莫居凡好像能听见温时宇的心跳,一下一下像隻藏羚羊一样顶得他的心脏生疼。没错,莫居凡他心疼了,他第一次听见温时宇哭,温时宇说想他了。
「你在哪里?我去找你。」莫居凡对着电话那端说,他的声音依然如装在透明玻璃杯里的温水一样乾净。
温时宇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握着电话,握了很久,他的嘴张了几次,可是一个音都发不出来。他从脑子给出的选项中好不容易挑了一个最简单的,深吸一口气,说:「苏子晨知道。」
「我去找你,等我。」
然后电话断线了。
他把手机还给施天其。
现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他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莫居凡低下头,空气中的尘埃飞舞着跳到他的睫毛上,他刚才做了什么?一切发生得像被人按下快进键一样行进得快速。画面一帧帧地滑过他的眼睛,在他的眼角闪出一道光辗转藏匿在太阳穴里,它们似有似无地擦过神经元触角带来的瘙痒感把莫居凡拉回了现实。
他回家拿护照,收拾了两套乾净的衣服让苏子晨把他送到了机场。
窗外的亮光透过大大的钢化玻璃照在莫居凡身上,还有七分鐘登机,手上的錶滴答滴答地走。他好像回到了几年前,那时候温时宇还在他的身边,温时宇帮他买了咖啡,温时宇看着他过了安检,可是他头也没回,因为他知道温时宇在看他,他一点也不用担心温时宇会不见。
登机的提示响起,他拿起行李通过了安检。
这次他也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温时宇在等他。
吴松揉了揉眼睛。这一个星期来他只睡了十个小时,程品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每天都会去看他。
抬起手腕看錶,差不多该走了。把桌面上打开的文档全部保存,把车开出了公司。
医生们称病人们待的地方为急性护理病房,目的是为了避免患者们情绪激动。
要知道所有骯脏的东西都有着一个官方正式的名字把它们罩着,他们称自己叫做雷锋,一切为人民利益出发。就像妓女也叫小姐,她们都说自己是靠体力运动赚钱的一样——当然,你没理由说他们的不是,第一,忽略期间过程,医院确实把病人好好看好了没让他们乱跑。第二,妓女们确实是靠着体力运动赚钱,而且她们很聪明地把“劳动”的“劳”字改为了“运动”的“运”字。
程品诺不在房间里,查房的医生告诉他程品诺去了日光浴室晒太阳。那是一个为病人设计的露天共用房间,阳光可以从外面很好地透进来。
程品诺坐在一张椅子上,阳光照耀着他的整个身体。他的头发长长了,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光。吴松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把手放在他的头上,阳光把他的头发晒得暖暖的,似乎还有一股淡淡的洗发精的味道。
「你来了。」程品诺说,他看着吴松,他没发病的时候看起来很安静,「温时宇怎样了?」
吴松把毯子披在他的身上,理理他的头发,说:「莫居凡去找他了。」
「哦,这样,」他点点头,「其实精神病患者的好处就是造成任何事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吧?法院怎么说?」
「如你所想,无罪。」吴松轻松地呼了一口气,抬头看着头顶的阳光。
「我差点弄死我自己和莫居凡,」程品诺笑笑,「除了发起病来会把自己陷入生命危险中其他也都还好。」
吴松没说话,程品诺的话像醒木一样敲得他心里一颤。
「我发病时他们总是给我吃安定文,」程品诺说,盆栽的阴影打在他的脸上,「你要是睡不好也可以吃那个。吃了那个后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知道了。」吴松瞇着眼睛笑,眼睛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然后他的背影消失在了门后。
「好。」程品诺说,他笑着,酒窝在他的脸颊上凹下去,小小的一个。
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拿了我的公司对我心存愧疚?我真后悔没连着你和邱柏榕一起杀掉。
他站起来,搬起一盆盆栽往地上砸去,陶瓷的材料碎了一地,他挑了一块尖利的往日光浴室外面走去。一位护工走到他面前:「你要用它做什么呢?」
关你什么事?程品诺没理他,指尖摸着尖锐的边角,他喜欢这种尖利的感觉,他想用它挑断一个人的颈部大动脉,他想让一个人温热的血液洒到他的身上,他想听听内脏掉到地上的声音。他不想伤害人,但是他会。
他感到有个人从后面把他拦腰抱起,紧紧地捆着他的手臂要去抢他手里的碎片。
你们怎么都他妈那么爱抢别人的东西?吴松也是,温时宇也是,莫居凡也是。你们怎么他妈什么都爱抢?
他用胳膊肘子狠狠捅上后面护工的肚子,他兴奋得有点手颤,他举起碎片,碎片的边缘在他手上印上一条条的伤口,血液一滴一滴沿着碎片边缘滴到护工的脸上。护工的瞳孔因为惊吓剧烈收缩着,碎片尖端在他眼里不断地放大。佔有优势的快感像要把他的大脑绞碎,他耳边好像响起了瓷片扎入肉体那种浑厚诱人的声音。
护工缩起腿,往他肚子上一顶,然后迅速按下他从后面捆着他的手:「快点,给他餵安定文!!!」
他的脸贴在地上,他笑着。
看来,比起我的东西,你们还是比较想要,命。对吧?
他放弃了挣扎,然后感到肩上一阵尖锐的疼痛。安定文缓缓地流进他的血液里。
他累了,他需要睡一会。
飞机在云层上空飞行,往下面看去是被云笼罩着的城市的灯光。
莫居凡有点睡不着,他在黑暗中看他的手心,之前被邱柏榕弄出的伤痕上覆盖上了新的伤疤,是车祸那时候添的,是疤,不是痕,它好不了。
温时宇送他的耳机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口袋里,这几年来他都没有换过耳机。
为什么不换?——人的问题一来了就会没完没了,为什么不换?为什么爱上温时宇?
举一反一,为什么不换?因为莫居凡他念旧。
为什么爱上温时宇?因为莫居凡他念旧。
—那为什么又要拼命升级一切电子產品的系统和软件呢?
—我不知道。
—看吧,温时宇和他留下的东西你都会像吸毒者渴望毒品一样想要佔有。
—那又怎么样?
—你待会就要见到他了,好好休息一下。
他抵达的时候纽黑文下雨了,空气中的燥热和灰尘被冲刷得一乾二净,流进骯脏的下水道里。莫居凡没有带伞,雨水打在他身上渗入衬衣的棉布里。凉凉的感觉让他打了个冷战,他拦了一辆车,咖啡被他握在手里,香气氤氳成蒸气在空气中散开,燻得他眼前有点朦胧。他想起大学的一次他和温时宇回家,他靠在温时宇肩上睡着了,太阳穴压在温时宇的肩胛骨上,体温透过衣服传到他的脸颊上,上面残留着和他一样的洗衣精的味道。顺着脖子一直看上去是一张完美的侧脸,上面散着白芒,线条像被橡皮擦擦过一样,模糊了那人的容貌。
他有多想见到温时宇。
车子在房子前停了下来,路灯上掛满了水珠,啪嗒啪嗒地滴到地上。周围安静得让他感觉得到时间正擦着他的耳尖快速地流动。白驹过隙。
他拿起手机给温时宇打电话。
温时宇正趴在桌子上睡觉,电话的声音吵醒了他,眼前的檯灯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摸到放在桌角的图钉,狠狠地被扎了一下,睡意顿时少了大半,他半瞇着眼睛找到手机,按下通话键:「喂?」
「我在楼下。」莫居凡说。被电波模拟的有些失真的声音传进温时宇的耳朵里,这比疼痛更能让他清醒。
他抓紧手机赤着脚往楼下跑去,心脏的跳动似乎都要撞上他的小舌头。要不然他现在为什么那么想哭?莫居凡就站在他面前,雨水流进他的眼睛里让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泼了水的油画一样模糊。
他不想说话,他觉得自己的声音现在一定很难听。
他一步步走过去,他走得很快,被水湿润的地面引出他在灯光下的身影,莫居凡的脸在他眼里越放越大。离莫居凡只有一步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流不出来的眼泪装在他的眼睛里,让他看不清莫居凡的脸。他突然想赌一把——
这算什么?游戏?他温时宇可一点也不想把他的人生当成游戏来玩。可是赌一把怎么样?我们不把它当真?
正当他在犹豫不前时,莫居凡一步迈过去把温时宇抱在怀中,他的鼻樑重重地撞到莫居凡的胸骨上,他一点也感觉不疼,可是他哭了,莫居凡的心跳传到他的额头上。
这就是他想要的。
让莫居凡迈出最后一步。
是的,就是这样,他想要的是一个敢为他迈出最后一步的人,而不是一个肯为他放弃终点的人。
谢天谢地莫居凡就是这样的人,他需要的人,也需要他的人。
他们在雨中接吻。
他们在房间里疯狂地做爱。
炽热的皮肤让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烧了。
一切都像树木在春天抽出新芽一样理所当然。
「你是我的。」温时宇凑上去舔了舔莫居凡的嘴唇。
「我是你的,我自愿的,」莫居凡笑,他的眼睛里闪着光,碎碎的像屋簷上的水珠砸在地上溅出的水花,「那么,你也是我的吗??」
不自信的提问让温时宇心脏像被什么用力拉扯了一下。他的手环上莫居凡的脖子:「我当然是你的。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
你把你的全部都给了我。
那么,现在,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
它们也全部都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