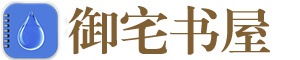53
作品:《是,将军》 算一算,韦彧已回到北齐近半载,与数年前她同时肩负军务及虎牢宗主、不时还需打理府中事宜的岁月相比,如今她虽失了自由之身,可除了偶尔打理这些年记录府中支出的帐本、逗弄肖府中仅存的两名幼苗之馀,间暇时间皆随心所欲,过足了她幼时一心渴望的安生日子。
此时,她慵懒地倚在偌大厢房中显得十分突兀的贵妃椅上,身下铺上先王御赐的玉蝉真丝被,敞开的画册稳妥地掩于面容上,遮去了晒人的日光,假寐着。
「能思过思得像将军这般处之泰然,委实不容易。」一股轻扬悦耳的嗓音凉凉地讽刺道。
「太使若欣羡,大可犯个欺君大罪。」韦彧拿下画册,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衣领,翻身坐正,拿起茶几上的桂花香糕,咬了口,慵懒地笑道:「以王上对常太使器重,定捨不得要您一命的。」
「伶牙俐嘴的ㄚ头。」常乐斜瞥了眼韦彧,对比当年神清气爽百倍不止的肖筠无奈一笑,放心道:「昨夜王上见过杨碇后果然向李瀧道出当年你与元镜的意思,别的不提,太子党欲弹劾你的那群文官今晨果然都及时收了口。」
韦彧欲添茶的手一顿,没露出半丝意外之色,垂眸沉吟:「是吗?」
接过韦彧递来的茶水,常乐熟门熟路地摊上一旁的贵妃椅上,低叹:「不过咱让人潜入东宫复抄出来那份参你的奏书写得太鉅细靡遗,要是不知晓,我还以为那些小道消息是你自个放出去的。」
韦彧瞥了常乐一眼,挑眉不语。
常乐顿时脑子一白,俐落地跳起,一把抓住韦彧的衣领,质问:「你什么意思?那些消息真是你自个放出去的?要是那奏书真到了戎王手上,就是戎王有心护你,你也必死无疑的。」
「要是不让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为了此封奏书而死,又如何能引出躲在李瀧羽翼下的杨碇?」韦彧轻轻一笑,似已完成多年宿愿那般平静,叫人疼到心坎里。
常乐低问:「你就这么不怕死?」
「常乐。」韦彧轻唤,自嘲地开口:「我是想活,想活下去到都快发疯了。」
眾人皆道肖筠是肖家歷代最为冷淡沉稳的家主,却不曾想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会哭会疼,也有自己想要得快发疯却不得之的事物。
常乐双手无力地垂下,整个人像洩了气的皮球摊回贵妃椅上。
「若非你在早已安插人手在太子一党中,我怎么也猜不到李瀧到了这般田地仍不愿放过你,竟与眾臣联手弹劾你男扮女装,为大隋所用一事。」常乐沉重地叹气,端详一圈此刻自顾自品茗的韦彧,跟前之人静如止水的褐眸一贯透出几分薄凉,脑中浮现韦彧过往战时佈阵的縝密,她心中顿时明瞭了几分,问:「你早猜到李瀧知晓真相后会如此?」
韦彧不发一语地拾起椅上的画册,目光流转,眉间揉着当年昭显将军独霸北方的英气,挺拔身姿八风不动,举手投足尽是歷代忠臣之后的坚毅。
「他要的是濂王府倒台。」静默了半晌,韦彧红唇微动,口吻平常得好似在谈论今日的天气般。「如此,他大不会这般艰辛地将我从大隋押回北齐后,轻易地放过我。」
见韦彧彷若旁人般点出此事,好似与之没有半点关係,常乐忍不住叹气,再问:「你又是如何猜到李瀧会因此而收手?」
「自两年前开始,东宫不止一次的金援肖家,次次金额不小。」韦彧拿出纪录肖府大大小小支出的帐本,神情飘忽不定地解释:「我私下探过老总管口风,此事不假,他还说每年李瀧在我落崖那日都会到我牌位前亲手焚一炉香,此事他做得极为低调,从不愿意让他人知晓,你说,他图的是何物?」
常乐乍闻此事,震惊不已,久久深陷在思绪中难以自拔,「什么?」
「是心安。」韦彧笑得云淡风轻,一如她以五千兵马力敌辽金三万大军时的无畏,轻问:「如此一来,若他知晓当年我嫁与阿镜背后的意义,又会如何?」
她就像头伤后休憩多时的母狮,早已养足精神潜伏在暗处,牙间闪烁嗜血光芒,只待在关键时刻给予敌手致命一击,她不禁想起两人初见时,生有一副倾国容貌的女将隻身立于丘壑,笔直身躯一袭牙月盔甲,披肩的赤色大氅随风飘扬,对常乐的医者之仁,落下冷硬的一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为教养出有利巩固李氏皇权的后代,肖澜的手段可谓心狠手辣,对唯一的孙女肖筠,更是苛刻得令人不忍目睹,她听李元镜提过,肖筠十岁那时的生辰,肖澜要她徒步走过近百米烧得发红的黑炭,年幼的李元镜立于肖澜身侧,吓得瑟瑟发抖,好一会都说不出话,可与他同龄的肖筠二话不说地褪去鞋袜,彷彿未见到足下踏的是何物,眼都不眨一下地走回全程,烫掉一大片肉仍硬气地不吭一声。
在这般近乎病态的教导下,养成肖筠凡事吞入腹中的忍隐性格,直到她十三岁亲临沙场依然。
思及此,常乐忽然明白为何肖筠一年总有大半的时间寻遍名目留在安山,或许这偌大的肖府之于她才是深埋心底,难以言明的牢笼。
「接下来你打算如何?」
「不如何。」韦彧淡笑,慢条斯理地翻开画册,用手勾勒在心中描绘千万遍的轮廓,问:「你何时啟程?」
「时辰不早,马车已在外头等候。」常乐缓步走向牢门,临前忍不住回首,有些迟疑地问:「你真不争?」
韦彧毫不考虑地摇头,反问:「他从未心系龙位,争了又有何用?」
「叶彣那处……」
「不是有你吗?」韦彧打断常乐接下来的话语,笑得没心没肺,决绝道:「何况,叶彣和我肖筠早没了干係。」
见状,常乐满腹话语怎么也再道不出口,久久盯视跟前随着岁月流逝越发沉着从容的绝色,似笑非笑地轻叹:「要我是李瀧,寧可和元镜对着干,把朝堂渲染得腥风血雨,也不愿与你有半分过节。」
韦彧随之浅浅地笑开,喜悲未明地笑道:「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