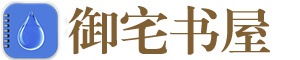4
作品:《英语家教 (也是克味小文学)》 下午,我洗了澡。镜子里我的肤色仍然显得有些暗沉,气色不是太好。我涂了点乳液和隔离,想尽可能把皮肤弄得匀净白嫩一点。
我这是在干什么呢?其实我的脑海中隐约闪过这个念头。明明我的生活是一团糟,明明被这些怪异的事折磨到心力交瘁,但我竟然还在想着做点什么能让自己见到Andy的时候好看一些?
我大概真是病得不轻。
但我像是不受控制,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化妆品和衣服上。看见自己的黑眼圈被遮盖住了一些,肤色也勉强提亮了,我甚至扯出一个莫名的笑。
我的外甥仍然在看动画片,而且pad音量仍然是那么大,我在楼上都能隐约听见。卡通人物一阵阵尖锐疯狂的笑声超声波一样穿过楼板刺进我的耳膜。
王姐没有制止他。她肯定不会说什么的,保姆怎么会去说主人家的小孩?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我表姐一家人都不太会管教他。毕竟这是一个在夫妻四十出头才要上的孩子,打了很多催卵针,失败好几次才成功的试管婴儿,这个过程无比艰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不溺爱他,怎么可能不让他为所欲为。
但就是很奇妙地,他们还是很在乎他的学习,相信他很聪明,花大价钱给他找老师找补习班,如果真的那么溺爱,为什么干脆什么都不要管了?英语考50就50,之后上个职校随便找个工作不是也很好吗?反正他家也不缺钱。
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也开始变得阴暗起来。我摇了摇头,试图驱散脑子里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因为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自己对我外甥的恶意。之前我虽然不想管他,也不喜欢他,但我没有过这么明显的恶意。而刚才,我分明地感觉到,自己就是不希望他好。
我强迫自己的注意力回到那些化妆品上去。我吹干头发,画了眉,勾了眼线,在脸上扑一层散粉,然后涂上口红。但镜子里的我并没有变得更好看一些,反倒看上去更加奇怪了。明明化妆品都是提升气色的产品,但我看上去,却像是戴了一层面具,了无生气。
也许无论如何总比我蓬头垢面的样子强吧,我想。
一阵非常嘈杂的音乐声从门外传来,声音越来越大。听起来像是我外甥拿着pad上楼了。那是一段很简单的旋律,有点迪士尼动画里的配乐那意思,但音色很浑浊很扭曲,不断地重复着。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想用一个比较耐心和温和的态度说说我外甥。
门外并没有人。
整个二楼,没有人。
但他的pad放在二楼公共区域的一张茶几上,还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那段旋律。
我拿起pad,里面竟然是一段卡通版的少儿英语?
一只长得有些像佩奇的粉色卡通小猪,一头黄色的卡通长颈鹿和一只绿色的卡通猴子,每人举着一张上面写着单词的卡片,随着旋律蹦蹦跳跳,左右摇摆。
等等,但那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吗?
“What You thinking”
卡通动物们欢快地改变了队形。
“What thinking You”
接着,它们用夸张的声音,开始朗读这几个单词。
“Follow me~~~~~~~”
“What~~~~”
“You~~~~~”
“Thinking~~~~”
“Think~Think~Think~Think~”
我猛地按住home键,pad屏幕熄灭了,一切安静下来。
我拿着pad下楼,王姐刚好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先是愣了愣,然后笑了,老实说我觉得她笑得有点尴尬有点敷衍。
“化妆了?要出去呀?”
“啊,可能晚点出去见个朋友。”我有点不自然地说。我化的妆真的有那么失败吗……
“哦,带轩轩一起去?”
对哦。
Andy约我出去吃饭,我带我外甥去也不合适吧。
“X轩呢,您看见他了吗。”
“轩轩在睡午觉呢。”
“一直都在睡?”
她的眼神有些疑惑:“不是啊,玩了会儿才去睡的。”
我轻轻推开我外甥的房间门,窗帘拉着,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他蒙着头,被子下面一个拱起的轮廓。
“要不……您看您今天下班之前给他准备点吃的?” 我试探着问,“我估计5点半左右走,7点就回来了。”
她看我一眼,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又没说出口。
“行啊,有现成的排骨,我走之前给他热热放桌上。”
我知道她怎么想我,肯定觉得我不是个负责的小姨。
但我就算在家也只会给我外甥点外卖,难不成还要我动手给他做叁菜一汤?
我把pad放在一边充电。回头,发现王姐还站在原地直直地看着我。
我心里有点发毛:“怎么了王姐?”
“啊,没事。”她好像被从什么状态里叫醒一样,“我刚才想着有些东西家里没有了,要是你出门能不能顺便捎回来。但我这脑子,忘了是什么东西。”
“那行,您想起来告诉我。”
我临出门的时候,王姐跟我说,让我买一些保鲜袋和洗涤剂回来,大桶的那种。
我找到那家川菜馆,很小的店面,是在背朝主干道的一边,里面只摆了几张桌子,但竟然都坐满了,还有人站在外面等位。Andy坐在很靠里的一张桌子旁,在翻看菜单。
“嗨。”
他抬起头:“啊,据说这家店人一直都很多,所以我早点过来占位置,看来我还挺明智的。”说着他晃晃手里的菜单:“吃什么?我感觉他们家的双椒味燃面不错,我给咱俩都点了大份。”
很快,服务员就把我们这桌的东西送上来,两碗巨大的燃面,几碟凉粉口水鸡之类的小菜,两瓶橙子味的北冰洋。
他熟练地用起子开瓶,递一瓶汽水给我。
“这……好大碗……我吃不完啊,可能会剩。”我看着那个巨大的海碗,目瞪口呆。
他很严肃地看向我:
“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吗。”
被他这么一说,我的确觉得剩饭是件很罪恶的事情,遂点头:“好吧,那我尽量吃完。”
他一笑,有些促狭:“好。”
有一说一这家店的燃面和小菜都很不错,味道正宗。他吃得很斯文,果然是“好看的人做什么都对”。
我感觉很放松,胃口似乎也好了起来。于是我也就不甘其后,埋头苦吃。
直到我们面前的碗都见了底。
他瞪大眼睛:“你都吃完了啊。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
好吧。
是我再一次过于认真了。
但我能说什么呢。
“你心情不好吗?”他突然问。
“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工作忙?” 他的眼神带着几分探究。
我摇摇头,换了个话题:“能陪我去趟旁边超市吗?我买点东西。”
我们去超市,买了王姐要的保鲜袋和洗涤剂,放在他的车后座,然后回家。
回到家,由于王姐走的时候关上了空调,屋里颇有些闷热。似乎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异味。
Andy肯定也闻到了,我看见他微微皱起了眉。
“你们家是什么东西坏了吗?”他问。
我也纳闷:“不知道啊?按理说不会呀……”
我先把空调打开,然后去叫我外甥。他已经起床了,在自己屋里,拿着手机打游戏。反正他不是和手机长在一起就是和pad长在一起,习以为常,喜闻乐见。
“你吃饭了吗?”我问他。
他哼出一声:“啊。”
“别玩了,老师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准备上课。”
他不情不愿地放下手机。
我想到他下午看的那些邪典东西,顺便提醒一句:“对了,以后你别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
他斜我一眼,一脸“你管得着吗”的表情。
“老师让我看的。”
“你瞎扯什么呢,老师能让你看那些东西?” 我嘴里是那么说,但心里还真是抽了一下。
我外甥提高了嗓门,认为我在无理取闹,颇为委屈。
“就是老师让我看的你凭什么不让我看老师布置的作业你管得着吗——”
Andy走进来:“怎么了?”
刚好。我把pad伸到他面前,屏幕解锁以后还定格在下午的视频画面上。
“这个视频,是你布置给轩轩让他看的吗?”
他点了一下屏幕上的播放键,看了几眼:“是啊,这是我们机构的一个少儿英语视听课,怎么了?”
屏幕上的卡通小猪、长颈鹿和猴子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用非常活泼纯正的美式发音读着简单的日常对话句子。
“Follow me: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Peter. What’s her name? Her name is Sarah…”
我愣住了。
“怎么了?”他又问。
“额,没事。” 我吞吞吐吐地搪塞,“我看他天天都在看这个,感觉他有点沉迷电子产品,就……”
“嗯,小孩沉迷电子产品这确实是个问题,家长也要管理一下每天的使用时间吧。” 他说。
“哎,对。”
“那我们先上课了?”他说。
“好。”
我外甥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在我走出房间之后把门很重地摔上。
就这态度我也没法管理他的电子产品。
我思忖着,究竟是我的脑子哪里出了问题。
我是真的病了吗?曾经我听一个领导说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神经病。对于这句话我深表赞同,但我理解,他说的神经病指的应该是人们自身的一些性格缺陷。像我今天下午这么严重的神经病,大概就得去精神病院了吧。
我不想生病,也不想进精神病院啊。
我究竟是怎么了?
但我能确定,即使开了空调,我仍然能闻到那股若有若无的异味。
餐桌上没有剩饭,我打开冰箱,冰箱也没断电,冷冻室和冷藏室都好好的,冷冻室里满满的用保鲜袋装着的生肉,其实家里没几个人,搞不懂王姐一下子买这么多肉干什么。
接着,我打开厨房门。我想是不是厨余垃圾没倒,或者下水道有什么堵住了。
那股味道扑面而来。
厨房的墙上、灶台上、地上,全是鲜红的碎肉末,混和着白色的脂肪和筋膜组织,有的甚至溅到了抽油烟机的管道上,厨房天花板的灯罩上,颤颤巍巍地悬挂着,似乎马上就要掉下来。
就像是,一个人在厨房里爆炸了,炸成了不比饺子馅大多少的小块。
我试着跨出一步,地板油腻黏滑,我差点摔倒。
我跌跌撞撞地扑向厨房水槽,拧开水龙头然后吐了个痛快,把那顿美味的晚饭吐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不剩。
-----------------------------
【显然,由题可得,王姐把装修师傅碎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