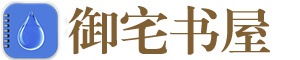第155节
作品:《家祭无忘告乃翁》 低头望着搭在胳膊上的那只手,方县令嫌恶的拂开,他是正经科举出身,最看不起街头混混,想到自己竟与这么个玩意为伍,一边唾弃自己一边心生埋怨,“你还有脸说?要你们做事谨慎点,这次冲撞到贵人了吧。”不说谭盛礼在京城的威望,单说在绵州,衙门都得看他面子。
而他不过区区县令,方县令拍了拍衙役抓过的地方,眼底闪过丝阴狠,“我辞官归隐,你们另谋出路吧。”
衙役慌了,他以前名声恶臭,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好不容易做了衙役名声好点,哪舍得继续回去当地痞,他问,“是不是谭老爷准备把我们的事上报朝廷?要我说啊大人,你还是心肠软了点,左右在咱们地界,那人是死是活还不是咱说了算?”
无毒不丈夫,对付那种读书人,还是得用拳头说话。
方县令没吭声,幽幽盯着衙役看,看得衙役心里发毛,听他肃然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门下学生一人一滴口水就能把他们淹死。
“不就是帝师后人吗?挡我路者,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我不敢。”方县令直言不讳。
“此事不用大人出面,我们兄弟就能搞定,你放心,就算事情败露也绝不会供出大人你的,只是大人,我家还有两个弟弟,你看...”
方县令回眸看了眼客栈,没有作声,走出去很远才哑声说,“你若出了事,你弟弟就顶你的职位。”
富贵险中求,他已经不是那个胆小怕事的方举人了,谭盛礼再有威望,死后不过一培黄土罢了,自己还怕他不成?他提醒衙役,“做得干净点,被人看出破绽别怪我没提醒你。”
衙役咧嘴笑了,“大人请放心。”
他们虽没杀过人,但还没见过杀猪?
杀了剁成块煮熟喂狗,谁分得出是人是猪啊。
谭盛礼不知危险降临,方县令离开后,他上街打听方县令为官如何,刚开始人们支支吾吾不肯说,有人开口后人们抱怨就多了起来,谭盛礼心里有个盘算,见礼后就回了客栈,他走后还有人忐忑地问同伴,“怎么今天这么多人打听方县令,会不会出事啊?”
看他们模样非富即贵,能为咱们做主就再好不过了。
谭盛礼不知衙役对他起了杀心,回客栈后,他给两州知府各写了一封信,又给京里叶老先生写了一封,方举人是他学生,为官不为民做主,竟伙同地痞混混欺压百姓,为师失职也,谭盛礼没有指责叶老先生的意思,但学生做错事,做老
师的难辞其咎,只望叶老先生日后收学生谨慎些吧。
将信送出去,这才回客栈休息,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听人呐喊说走水了...
谭盛礼被惊醒,外间传来乞儿的声音,“谭老爷,火已经扑灭了,你接着睡吧。”
楼下柴房走水,得亏掌柜盯得紧发现及时,否则就酿成大祸了,自谭盛礼进门掌柜就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生怕哪儿招待不周怠慢了贵人,刚刚有个人鬼鬼祟祟往柴房去他便多了个心眼,谁知去后院查看,那人正往柴上泼油点火,掌柜失声大叫,逢乞儿他们回来,掌柜要他们赶紧去楼上喊谭盛礼。
得知谭盛礼在楼上睡觉,唐恒不由分说地去井边打水救火,风驰电掣舍我其谁的架势吓得掌柜以为谭盛礼睡在火里的呢。
不管怎么说,火扑灭了,除了损失点柴和油,客栈没有更大的损失。
以为谭盛礼他们会清早离开,谁知半夜突起兴致要走,小镇没有宵禁,马车能出城,掌柜在柜台边拨弄着算盘,见他们下楼,愁眉不展地迎上前,“谭老爷要走了?”
掌柜踟蹰,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有人会在他客栈纵火,直至傍晚送菜的农户来,两人聊起此事,农夫问他是否得罪了什么人,纵火不是小事,惹出人命是要坐牢的,普通人谁敢啊。电石火光间,掌柜想到了昨天跪地不起的方县令,顿时脊背发凉,他低着头,小心翼翼问谭盛礼,“此去黔州可有人前来接应?”
“此去祭拜故人的。”
就是没人接应了,掌柜有些着急,看向谭盛礼怀里歪着头酣睡的孩子,温吞道,“谭老爷没来过黔州吧,以前黔州土匪窝子不少。”
唐恒听不懂掌柜的话,他不喜欢黔州,但毕竟是他故土,不爱听人抹黑,呛声道,“官府不是都将其安顿好了吗?”
没犯过大错的重新做人,有罪的坐牢抵罪,罪孽深重又拒不从良的直接排官差剿匪,怎么就还有土匪了?
他语气冲,掌柜不好再多说,让谭盛礼稍等,去后院拿了个包子出来,讪讪道,“这是内子做的,黔州特产,谭老爷尝尝吧。”
唐恒嗤鼻,他,土生土长的黔州人,从来没听说包子是黔州特产,哪怕掌柜送包茶也比这强吧,不过看谭盛礼脸色似乎很喜欢,临走时还多给了几文钱,“多谢掌柜了。”
唐恒毫不留情地告诉他,“表舅,你被骗了。”
谭盛礼没吭声,夜里寂静,车轮辗过青石砖的声响格外响亮,马车行驶得很快,快得车里的唐恒坐不稳,很想冲外边抱怨,但看谭盛礼神色冷峻,硬是憋着不敢吭声,“表舅?”
“嗯。”
唐恒没话了。
片刻功夫,马车突然停了,唐恒撩起车帘看向车外,借着车里的光,看清了车外情形,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车轮极其蹩脚的辗过两侧草地,唐恒:“怎么不走官道?”
耳旁传来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旁边有簇竹林,唐恒不解其意,但听谭盛礼轻描淡写道,“
砍柴如何?”
唐恒:“......”谭盛礼觉得他白天偷懒了?他怎么可能偷懒,他要是偷懒乞儿就会跟着学,柴少卖的钱少,谭盛礼花出去的就多,分到他手里的就少,他怎么可能偷懒!!
谭盛礼太瞧不起人了点。
“怕死吗?”谭盛礼又问了句。
唐恒不说话,默默抄起刀就任劳任怨的走向竹林,只是这时节没什么干竹子,好在谭盛礼要求低得很,只要新鲜的竹子,两头还必须是尖的。
谭佩玉抱着如兰站在边上,郑鹭娘则提着灯笼照明,谭盛礼和朱政袁安在小路上不知嘀嘀咕咕些什么,唐恒隐隐觉得气氛不对,抵了抵卖力砍竹子的乞儿,“表舅是不是被烟熏坏脑子了?”
乞儿:“......”
谭老爷是怕客栈走水乃有人故意为之吧,方举人为人虚伪,保不齐杀人灭口,见唐恒几下就砍断了竹子,手法熟练,他没有多言,无知者无畏,他问唐恒,“恒儿怕死吗?”
唐恒:“......”
看了眼不远处的谭盛礼,唐恒挺起胸膛,“不怕。”肯定是表舅考察自己是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怎么可能怕死,永远不会怕死的。
乞儿笑了,手下愈发用力,“我也不怕。”
想到掌柜给谭盛礼的包子,乞儿塞给唐恒,“谭老爷让我拿给你吃的。”
唐恒坚决摇头,“我不吃,给如兰吃吧!”他要好好表现,争取多分点家产,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包子就功亏一篑,他又说了一遍,“包子给如兰吃。”
“恒哥...”乞儿必须说句实话,“其实你和振兴哥很像。”
唐恒:“骂人也不带这么骂的。”
乞儿:“......”
他们动作很快,一盏茶不到就砍了很多竹子,且削得尖尖的,乞儿给朱政他们抱去,两人跳下挖好的坑,将竹子插.进去,然后在上边铺上稻草,往前还铺了几步,看着像哪个农户除草后扔在路边没来记得收走的,农户们除草,草都背回家晒干当柴烧,有那嫌湿草重的,随手扔在路边晒着,晒干了再背回家。
因此有主人的田地旁放着草基本没人会拿,这是农户们默认了的。
一切准备妥当,朱政问,“咱们是找地方藏起来还是继续赶路?”
“等着吧。”他已经给两州知府去了信,只要拖住他们,几个时辰内就会有答复了,以防两州知府互相推诿勾结,他特意让谭佩珠写了封信给平安书铺的掌柜,那个掌柜收到信会想法子的......守在这是以防追来的人不是衙役是普通人,掉进陷阱就遭殃了。
让朱政和袁安将马车藏进草丛,他们躲在暗处等着。
唐恒琢磨出点意思,“有人追咱们?”他怎么不知道?
谭盛礼摇头,“不是追,是杀吧。”
唐恒惊住了,杀他们,谁这么有眼不识泰山啊,谭盛礼可是国子监祭酒...等等,他瞪大眼睛,“客栈放火的人?”
“
☆、第185章 1854
唐家是商籍,处心积虑地想攀关系无非是想找个靠山,唐恒虽是唐家人,但自幼仇恨他们,恨不得他们死绝,真要把唐恒接回唐家,家宅恐怕难以安宁。
郑鹭娘就不同了,她是女子,女子本弱,寡妇尤甚,郑鹭娘这些年没少被人非议,有人传她与很多人眉来眼去不清不楚,邻里就没有妇人不讨厌她的,同意这样的人进府,不止会让她感恩戴德死心塌地,而且能牵制住唐恒,但凡郑鹭娘在,唐恒就不敢来唐家嚣张。
生恩不及养恩大,唐恒毕竟是郑鹭娘带大的。
偏偏遇到唐恒那个油盐不进的横生出枝节来,唐老夫人不喜道,“此乃我唐家家事,谭老爷便是帝师转世也不能过问咱们家事吧?”
说到最后,她自己不确定了。
帝师啊,那样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怎么就不是唐家亲戚呢?
“祖母,他不是咱能惹的,没听他说去衙门说吗?这位谭老爷做事雷厉风行,亲儿子都能亲手送进监牢,何况是咱们了。”唐复不明白唐老夫人心里打什么主意,在他看来,父亲使的手段上不了台面,真闹到官府,保不齐被安个逼良为娼的罪名,那可是重罪,花多少钱都把人赎不出来。
而且官府看在谭家的份儿上会不会报复他们都不好说,唐老夫人想想也是,别引狼入室害了儿子,她不敢再提郑鹭娘的事儿,而唐老爷和几个儿子,更是满目惊惧的去客栈见谭盛礼,担心谭家觊觎他们家产,硬是买了身旧衣衫穿着。
他们去客栈找谭盛礼时,唐恒正跪在桌边求谭盛礼。
唐家人欺人太甚,郑鹭娘将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唐恒担心她有个好歹,“表舅,我不要谭家家产了。”他表情凝重,“我能否求表舅一件事。”
黔州民风保守,女人只能依附男人过活,郑鹭娘带着他受了很多冷眼嘲讽,他以为郑鹭娘不会将此放在心上,直至刚才郑鹭娘告诉他离开黔州回夫家,郑鹭娘是嫁过人的,成亲不到半年丈夫就死了,夫家人嫌她晦气要将她嫁到很远的地方去,姐妹情深,他母亲想法子将人接到家里来。
然后家里出了变故,就剩下他们两人,郑鹭娘在母亲坟前发誓要把他抚养成人,这些年任劳任怨地照顾他,不是没有男子上门求娶,郑鹭娘都没答应,还说有他就够了。
他心里一直都这么以为的,打心里将其认作自己亲娘。
没想到郑鹭娘会想离开。
黔州的宅子已经卖了,他们没有落脚的地,郑鹭娘在黔州靠什么过活?而且唐家那群人不要脸,他不在,只会不断地找茬...
“表舅,我只求你一件事...”唐恒仰起头,像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你...能否娶我四姨,你放心,我们发誓不夺谭家家产。”
人们说他四姨命苦,男人死了,好不容易捡个儿子养老送终,可儿子攀上高枝了,可怜她人老珠黄无依无靠,还说他四姨那些年就该再嫁的,否则早有自己的子孙能安享晚年了,类似的话唐
恒以前就听过不少,但从没像现如今难受。
明明他读了书识了字,将来会有大笔的家产,人们为何笃定四姨跟着他会过得不好。
唐恒想不明白。
谭盛礼垂眸,扫过脸颊淤青的唐恒,他驼着背,神色沮丧又满含希冀,“你四姨呢?”
“在房里,要不是大表姐听到她屋里有动静,没准她就背着包袱偷偷走了。”明明说好相依为命的,郑鹭娘却要离开了,谭盛礼看了眼桌上的书,“先起来吧,我去看看她。”
恶语伤人六月寒,世人眼里,郑鹭娘守着外甥不嫁是不被理解的,如今看唐恒改邪归正,不乏眼红羡慕者乱说,就像赵铁生考中秀才后不也是这样的情形吗?
谭盛礼刚敲响郑鹭娘的房门,唐家人就到了,所谓男女有别,他们看谭盛礼堂而皇之的随郑鹭娘进屋,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底愈发害怕。
原来,谭老爷中意郑鹭娘!
几人面色惨白,缩着脖子,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准备等谭盛礼忙完正事再说。
谭盛礼隐隐明白郑鹭娘心里想什么,郑鹭娘不惧流言蜚语也要独自抚养唐恒,她做什么都是为唐恒好,唐恒以前混,做事不着边际,如今读了点书,郑鹭娘就担心自己是否拖累他了,女子柔弱,但为了家人什么都能牺牲,唐恒祖母是,谭佩玉是,郑鹭娘也是。
“恒儿很担心你,他满身恶习但真心想孝顺你给你养老。”
郑鹭娘背着身整理包袱里的衣衫,语气听不出异样,“我知道,只是我有手有脚的,哪儿用得着他给我养老。”
“他说你同意了的。”
郑鹭娘顿住,又说,“那时他年纪小,我自是顺着他说,我夫家在黔州东边小镇,离得不远,他要是想我了随时来便是。”她公公早些年就过世了,就婆婆还在,饮食起居需要人照顾,妯娌来信问过她,若想回去回去便是,但要照顾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