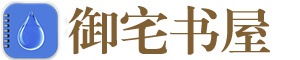99不可知
作品:《[NPH]人鱼玫瑰abo》 顾家几个alpha坐在一起商议迎回全新的顾珝的琐事,在来回的交谈过后,达成了一个共识:彻底斩断顾珝和厉轻的关系,不为别的,独独因他痴狂到自杀。在联邦,自杀当然合法,但像顾珝这样的alpha,他为了那样渺小的原因,开枪打死邻国王子,再杀害自己,这已经成为全世界都议论纷纷的丑闻。他已经成了被耻笑的对象,和那个被帝国王庭宣布彻底决裂关系的废王妃一样,不抛头露面。
大哥顾焱提议:“在阁楼原址上建一座新宅子,先供他住。”
二哥顾凛提出担忧:“他醒来以后什么都记得,或许不应该马上回家来,等我再做个手术再让他回来吧,见到厉轻……会不好。”
“有什么不好?他有胆子死,没胆子见我们?先让他回来,我想听听他到底后不后悔……”
顾凛看向顾息烽,“叔叔觉得呢?”
顾息烽点了头:“他回来以后先让他在院子里跪着,跪个三天也不过分,不知轻重的东西,不能就让他一忘了之,就是要他记得自己的耻辱,他才会真心悔改,以后才配合我们。”
顾焱也点了头,顾凛不便再多说,这件事就敲定下来了。
顾珝的新肉体要苏醒的那天,顾凛在实验室里忙得昏天黑地,赶回去的时候,顾珝已经被助手带到了顾家。他在门口短暂询问助手,他醒来是否异常,助手说:
“他异常平静,一句话也没说,这算异常吗?不过顾先生,任谁经历了他那样的事,也许都会变得平静吧。”
顾凛远远望着那个环视四周的背影,打发了助手,慢慢向他靠近。
-
仆人躲在角落窃窃私语。
顾珝的耳朵和眼睛都焕然一新了,听觉高度发达,视力清晰得骇人,但他经过那些人跟前,却仿佛既聋又哑。他们都见了他,都以为他也换了个脑子。但是,当他从温凉的培育仓中起身,没有一瞬间的情绪和记忆爆发的充塞感,他仅仅只有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轻盈念头——那就是坚持。
至于坚持什么,他一考虑到那份具体的情感就会双手颤抖,毁灭性的恐惧吞噬着他,他不知为何,没有大发脾气面目狰狞地去反抗,而是像一个圣徒被一股力量驱使着渴望靠近那个念头。
他大步穿过走廊,这双腿也和原来不同,有着更为强健的骨骼和肌肉。他不在乎这些,除了那个念头,他其他什么也不在乎,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那个念头牵引拉拽。
对于“死而复生”的弟弟,顾凛还在替他万般痛惜,他向他走过去,顾珝转过身。
顾凛眼神之中充满了对他的怜悯,就像他对自己的怜悯一样。他的目光没有得到回应,因为走到他跟前的顾珝——一具全新的肉体和一个未知态度的灵魂,忽视了他。
顾珝憋着一口气,问:“她呢?”
问完,他立刻吐气,感到无比安定。他只是在执行那个他内心的念头。
顾凛的表情转为更深的悲悯,同时夹杂着愤怒:“这回你是真的死了,怎么你的心,还不死?别说她了,顾珝,我带你去见叔叔和大哥,你向他们道歉,他们会原谅你的。剩下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不会让你一辈子痛苦。”
顾珝转动脖子,目光纯粹,纯粹得像真空中跳动的火焰,不沾一丝灰尘。
“什么是痛苦?”他似乎没认真听他说话。
顾凛拽住他的胳膊,提高音量:“什么是痛苦,她让你痛苦,你忘了你有多绝望了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摸摸自己的身体,你本该摸不到了,你本该死透了,永远也不可能还站在这儿打听她的下落。”
顾珝显得淡定许多,微微颔首:“可是哥不让我死,我现在也不想死,我现在就想知道,她——在哪?”
“你是疯了!跟我回去,让我仔细研究你的大脑,也许是发育得还不够成熟……”顾凛慌乱地拽着他往外走,顾珝如今的言行到了大哥和叔叔面前,他会受苦。
可是顾珝因为拥有了一副更强大的身体,轻易就推开了他的手。
“哥。”他认真地叫住他,顾凛觉察他眼中的固执,咬咬牙,道:“你先不要和大哥叔叔说你的这些疯狂的想法,等我给你做了手术你再回来和他们见面……”
顾珝为难地蹙眉,真诚无比:“为什么要手术之后我才能见他们?”
他如此执迷不悟,顾凛失了控:“你的事情都传遍了!你现在不该是这样的态度……你再继续找她会连最后一点自尊都没有,你还想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就别问她了,和她断绝关系吧。”
“纪丞死了。”他目光淡淡,眼睫低垂,“我还能堂堂正正地活,或者我还活的成吗?哥把我救活我也会死,所以我问不问她妨碍什么了?我活不活是谁决定?我自己已经决定过一次,但是我发现我的想法没有意义啊。既然我还活着,那我就想做活着的事,除了生死总还有别的念头……哥,让我见她。”
他深吸一口气,压住手的战栗,“我直接告诉哥吧,我醒过来的那一秒,我没有感觉到难受,我只感觉到她。你说我疯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就是想和哥一样继续和她纠缠,我就是要爱她……痛苦,什么是痛苦?远离她我就高兴了吗,靠近她我就更难过了吗?我不知道……哥,你又给了我一次生命,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但是我再也不想拐弯抹角地活了。我想要……”
顾凛静默地望着他,仿佛他意识沉睡的这一年,他的心已然跨越过千山,遥遥和他相望。
“爱!”
顾珝终于不再羞耻说出那个字眼,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抬起手轻轻擦过自己的眼皮,那里是热的,可是没有眼泪。他激昂的陈述吓坏了一旁的花匠,花匠瞠目结舌地盯着他看,仿佛他们已经不属于一个世界,花匠从未感到着急如此聪慧和自我爱惜,不禁震惊又鄙夷地低下头去,抚摸盛开的玫瑰。
顾珝不知羞耻地盯着花匠,偏偏就要对着他,魔怔一般说:“哥,我就想要爱,你说我可耻吧,我就是想要。”
他清晰的宣言被赶来的顾家家主一字不落地听见了,他急匆匆几步跨上来扇了顾珝两个响亮的耳光。和顾息烽一同前来的顾焱也神情严肃,加入了这场审判。
顾珝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但他的alpha的骄傲似乎失效了,他无所谓这些无意义的耳光和耳提面命的辱骂,再也感觉不到压抑的愤怒和同alpha相处的焦虑,他静静地站直身体,偶尔被拉拽得歪斜。
“你打够了,我要走了。”
顾息烽的军装乱了,眼角的皱纹紧紧拥抱在一起,他眯着眼睛恨他。
“命重要还是她重要?!”
他不假思索:“命。”
“那你还去找她,想再自杀一次吗?你知道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吗?一个刺客!为了一个omega先杀兄弟手足,再杀自己,不上台面的东西!”
“我的命重要,但我该死。我现在想找她,可以吗?”
“你是该死!要不是你二哥可怜你,你还能站在这里?”
“不能。”
顾息烽被气坏了,开始嚷嚷着让他滚。
“既然叔叔觉得尊严很重要,那就让厉轻出来。我们的名声肯定烂了,那我们都走,就父亲那样,和顾家撇清关系。”
“你还敢提你父亲?一点责任都不负的懦夫……”
顾焱拧起了眉,走上前去,道:“她是我法律上的妻子,不能跟你走。”
“法律?”顾珝难以置信,望着他笑了一下。
“大哥什么时候相信自己遵守法律了,大哥遵守的叫军纪。而且……大哥也不完全遵守。”
“你胡说什么?忤逆的狗东西!”顾息烽绕到他面前质问。
“有什么可忤逆的?我想把顾家的另一个耻辱带走也是忤逆……叔叔也知道顾家规矩多,所以我干什么应该都是忤逆,那我就做我想做的,让她出来,我想见她。”
顾息烽大口大口喘息,咬牙切齿,险些掏出枪把他再杀一次。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了,顾珝的确已经死了。至少在园丁眼里,在更远处对着他窃窃私语的下人眼里,他和他作为贵族alpha的尊严,一齐死了。
顾珝开始往前走,不顾一切挣扎着前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伴随着激烈的推嚷和叫骂,他走到了厉轻面前。
她早听见了吵闹声,站在不远处看了许久,她捂着嘴巴,久久才接受他还活着的事实。她再环视众人,明了他们看待顾珝的眼光如何,但她诡异地和其他所有人感觉都不同。她不觉得顾珝疯了,他应该是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了。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以至于刚再踏足人世,就吓坏了众人。
她歪过头,很注意地去看他的眼睛,是浅浅的蓝,是他最坦诚的眸色。
她慢步走过去,凑近了,依然惊异地地望着他,小心翼翼地挪到到自己的丈夫身边,顾焱立刻迫不及待揽住了她。
“别靠近他。”他警告。
她脆弱的身体禁不住alpha使劲勒,她低头抓住他的手臂,挣扎,顾焱把她勒得越紧,就在她快绝望准备屈服之际,另外一只强壮的手加入了她,替她掰开坚硬的桎梏。她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顾珝,深深吸一口气,往旁边踉跄半步,扶住柱子站稳。她才被允许出地下室不久,还没恢复过来,长久不见阳光,骨头发脆,再被挤压几下可能就要肋骨全断了。
不管如何,她感激地朝他点了点头,顾珝看着她的枯萎的金发。她一定什么都听见了,他不在乎,可还是会感到一些尴尬,被他竭尽全力消泯掉,他走过去,搀扶起她的身体,直白到不能更直白,说:“我爱你,我只要还活着,就不能不爱你,厉轻……我们走。”
厉轻全然愣住。
“你……”她开始哽咽,地下室里的昼夜光亮把她的眼睛都照坏了,加上蔓延的眼泪,她的视线逐渐模糊,看不清他的脸,只能依稀望见浅浅的蓝。
什么样一个人,脑子里有什么样的想法,才能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厉轻想不明白,她有些感动,并不是动容于他,而是动容于他这份可怕的爱,这是一种人鱼一族期望的爱,值得去托付唯一的珍珠的爱。她观察着他,感到绝对地不可思议。
顾珝不再想以前一样,好奇地探究爱人的心意,他静静等着,无所谓未来灾难与否,无所谓厉轻有多少情人,无所谓她有多恨他,又或者哪一天她也会爱上他。这些全都不重要了。
无所谓绝望,无所谓希望,他只去爱她。
他眨了一下眼睛,又听见顾息烽让他滚出去的骂声,他低身牵起omega瘦弱的手,“跟我走吧,去海边看看,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的信息素依赖症治好。”
“我不去……”厉轻抽回手,推开几个alpha关切的手臂,走到房间里把坐在角落缩成一团的珍珠带到他们面前,她尴尬地擦擦脸上的泪。
“珍珠在这儿,我和他在一起。”
一年没见到母亲的珍珠眼神从纯真到尖锐,她有太多的愧疚填不满,她蹲下一边笑,一边哭,难堪极了:“我治不好了,离开顾凛就不能活。小丞生死不明,我必须要对珍珠负责,我要留在顾家……我哪里也不去。”
顾珝稍稍失落,走上前去,把手搭在珍珠的头上,呆呆地问:“我们的女儿呢?”
厉轻缓慢地答:“小怜啊,她回海里去了。没有alpha愿意耐心养着她,她就被送回海里了……那是个好去处,我托人告诉她一定要往南边游,那里有我们的同族,她不会孤单的,她那么灵巧,猎人肯定抓不住她的……你不用担心。”
她安慰着他,更像是安慰自己。
顾珝蹲下来,直勾勾看着她,她受不住他直白且毫无负累的视线,别扭地扭过头去。
“南边,好,我明天就去南边的岛屿找找她,她愿意在哪里生活,由她。”
厉轻抽噎几下,露出一个凄惨但真实的笑容。紧接着,几个omega仆人在家主的示意下拥簇着她和珍珠离开,他们还没走远,就听见一声异响,回身一看,是顾息烽狠踹了顾珝一脚,随后愤愤离去。
所有人都以为今天的闹剧快要完了,可顾珝没有再像之前那般镇静,他直冲冲快走到顾息烽身前,挥起拳头打破了他的脸。
“人鱼在附近的海里那么危险,叔叔,除了你,不会有人敢送她走。”
他出了一口气,面不改色。
气氛挑衅,Alpha的暴烈的信息素窜满四周,顾息烽没有回击,相反只是擦去嘴角的血,骂了一句便大步继续走,一直拐到众人视线不及的地方,消失不见。
然后,顾珝就被赶出了顾家,是顾息烽的命令。他夜里在首都街头露宿半宿,稍稍休息后便化为狼形拼命奔向海边,向南去。他沿着海滩嚎叫,发出呼唤的信号,吓坏了大部分远在几公里以外的人鱼拼命向更远处逃窜,可他知道,自己的狼嚎声吓不退他的女儿,父女间有默契的感应。
他不停地努力呼唤,终于在快黎明时分在一处偏僻的海湾处再次看见他熠熠生辉的小人鱼。他们彼此交换了眼神,无需多说。他走上前,抖落背上的包袱,里面装着一件小女孩的裙子,是他出发时在店里的橱窗抢来的。他等待顾怜去榕树后面穿好裙子,她爬上他的背,抱住他的脖子,顾珝低了低头颅,感到无比的庆幸。
他驮着她回到城里,把她带到顾家,固执地在门口等着护卫兵去把厉轻找来。厉轻在顾焱的陪同下走到门口,她不能越过横隔在她和顾怜之间的铁门去,她颤抖地把手臂伸到门外去,眼眶比奔波大半夜的顾珝还要红,她缓缓蹲下,问她:“小怜是自己愿意回来的吗?”
顾怜眼里有担惊受怕,可还是一副天真的模样,使劲地点头,“妈妈……”
厉轻拉住她的手,大脑眩晕,在极度的欢欣冲击下,陷入昏迷。
顾珝看着她无力的关节和脖颈,呼吸急促,生生拉开两根铁棒,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试图将她从缝隙里拉出来。顾焱站在里面,很容易就打破他的企图,抱起厉轻往回走,顾珝便绕到后花园边,翻墙进了院子,先去门口把顾怜接进来,再无所顾忌在顾家走动,走到顾焱的卧室门口,几个强壮的随从兵才勉强将他拦住。
他现在这副身体体力大得惊人,顾焱早有防备。
“大哥。”
“你还叫我大哥,昨天连叔叔都不认了。”顾焱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顾珝推开身旁的人,“我可以不叫。”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大哥,但是却可以毫无alpha的样子,把自己的命都献给一个不爱你的omega,好不容易又活过来了,还想往火坑里跳。顾珝,你到底在想什么。”
顾珝眉眼神色淡淡:“Alpha的样子才害了我。”
“害了你?就是你现在这个不成样子的样子,才在最劣等的下人眼里都是没有一点脸面。”
“我不需要脸面,我不需要负担。”
“厉轻就不是负担?她割掉了生殖腔,有信息素依赖症,已经离不开顾凛做她的医生,你都觉得顾家规矩太多,那你想的自由,在她身边绝不可能有!”
“我的自由在我,不在她。”
“你受人束缚却说自由,可笑吗。”
“如果自由就是单纯的无拘无束,那我自由了,和街边的流浪狗有什么区别?”
“你真的疯了。”
顾珝对这句话丝毫泛不起波澜,“我想进去看看她。”
里屋沉默了,过了许久,顾焱走出来,他们面对面站着,他又重复一遍:“我想进去看看她。”
顾焱不说话,稍稍挪开身体。他擦过他的肩膀,忽然回过身问,“她的生殖腔,是她自己愿意割掉的吗?”
“omega没有生殖腔,对alpha有什么好处?当然只是她自己的愿望,顾凛有时候也和你一样疯了,陪她胡闹。不过可以算了,有珍珠,生殖腔也不那么重要。”
“要是没有珍珠呢?”
顾焱冷笑:“连你这个死人顾凛都有办法复活,何况造个婴儿?”
“那omega对你来说根本也不重要,就像厉轻的生殖腔,你该不在意了,还强留她干什么。叔叔把她视为祸害吧……”
顾焱冷下脸:“你该知道一个血统光荣的母亲对一个alpha有多重要!虽然她其他方面差了很多,但我可以慢慢调教她,亲生母亲才好。至少不能让珍珠像我和你二哥一样,从小没有母亲。”
顾珝不再言语,摆摆头牵着顾怜往里走。
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盯着她的脸看了许久,这张饱经风霜依然美艳动人的脸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丰富的表情,期待、高兴、喜悦、娇俏、恼怒、天真、羞涩、好奇、情欲、大方、茫然、失落、振作……到现在,仅仅剩下一张漂亮的皮囊,撑不起过分的欢欣了。
他掀开被子,把顾怜抱上床去,紧接着他自己也躺了上去。这是别的alpha的床,有同性的排斥的气息,他无所谓,拉住她枯瘦的手。
厉轻渐渐醒来,目光朦胧,望着天花板,呢喃:“要是小丞也像你一样活着,就好了。”
顾珝感受着胸口涌起的自然而然的嫉妒和愤怒,“他死不死有什么区别,他不可能再来找你了。”
“那你杀了他。”
顾珝沉默片刻,“是。”
厉轻叹息一声,她已经恨不动了,犹豫片刻,缓缓道:“你在帝国的时候收藏了很多人鱼的珍珠,那些珍珠是献给爱人的,被你拿走你会被诅咒的。”
“什么诅咒?”
顾珝眼神呆滞,大概猜到了她接下来的话。
“诅咒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会有爱人……”
顾珝听完,释然一笑:“那他们可以瞑目了,我的爱人她另有所爱,我将一生痛苦。”
厉轻揽住顾怜的身体,“小怜留下吧,我会照顾她的。我想睡了……”
“好。”
顾珝短暂地闭了会儿眼睛,翻身下了床,等他关上门,厉轻睁开眼睛,拉起顾怜的手亲了亲,幸好她累坏了,早就熟睡。
-
顾珝这样子招摇并不好,碰上认识他的市民,会出大乱子,顾焱派人悄悄跟着他,却发现自己实属多虑。他现在很是惜命,知道乔装打扮,往脸上身上抹写脏灰,穿着不知道哪个垃圾桶捡来的烂衣裳,混在下层民众里,过了半个月都没被人认出来。
顾珝白天在码头扛货挣点吃饭钱,晚上潜回顾家洗漱一番又马上离开,顾焱默许了他的进出,有天晚上他在卧室门口拦住他,问他为什么不干脆睡这里。
“睡这里和没被赶出去有什么区别?”
“你随便进出就有理了?”
“我没理,我是强盗,你可以抓我。”
顾焱垂眼看见他手边搭着一件和他穷酸模样极其不配的衣服,他冷笑了一下,“你现在还需要这些衣服吗。”
“不需要。”顾珝翻了翻衣服口袋,摸了好半天才摸出那颗深藏在衣服里的珍珠,他高举起珍珠对着光看:“这是她的珍珠。她说,这个东西被不是她的爱人的人抢走,那个人会被诅咒。我想……我可以替大哥和二哥保管。”
顾焱变了脸色:“迷信那些干什么。”
“我觉得她说的是真的。”顾珝把珍珠收进怀里的口袋,丢掉衣服,擦着他的肩快步走了。
两个月后,顾珝在码头租了一艘船,每天晚上干一点偷运的活儿,渐渐有钱把去租了个房子,就没再半夜潜回顾家。他慢慢地置办家具,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昼夜颠倒干了快半年,某天早上忽然听说,帝国和联邦停战了,顾家忙做一团。当天夜里,他又潜进去将在后院池子里待着的厉轻掳走。
他把她带到自己的船上去,拉开发动机一直往远处开。
厉轻坐在有些脏的毯子上,看着他的背影和波光粼粼的黑色水面,“你干什么?”
“怎么可能停战。”顾珝表情严肃,“除非他醒了……”
厉轻急忙挺直腰身:“真的?”
“我不知道,你先和我待一段时间。”
她望望四周,船中布置寒颤,“这里吗……?”
“不行?你到顾家来之前都生活在野外,这样的环境不适应?”
她抿抿唇,“有一股味道,很难闻。”
他回头看看发动机,“是机油的味道,停了散一会就没了。”
厉轻摸摸自己的金发,抬头看着破洞的船篷,轻轻说:“那再开远一点吧,远了能看见星星,安静些。”
顾珝如她所说,把船开得更远,一直抵达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他把毯子铺在沙滩上让她坐。
“只能坐一会儿,还是要在船里睡觉,有人袭击你我能快点反应。”
“哦……”和他单独相处,厉轻有些不适应,抓着毯子,坐得很直。“小怜和珍珠应该才睡着,希望顾凛去看看他们。”
顾珝直接坐在沙滩上,没了贵族的样子,“你和他关系还不错,这么相信他。”
厉轻将手搭在小腹上,“我答应过他,要爱他一些。”
顾珝的手握成了拳,“原来你的爱,还能给两个人。”
“可能吧。顾凛说他今天晚上才回来,你知道他离开这么久,去做什么了吗?”
“二哥这些天不在顾家?”
她摆摆头,“他去帝国了。”
顾珝稍愣,很快便感到心凉,“原来这就是二哥付出的代价。”
“是啊,他肯定成功了吧,小丞肯定……”
“是你主动要求的?”
“不是。我和他的孩子没了,怎么可能劝他。”
“二哥……”顾珝对着海沉沉叹息一声。
两人一时无话,不久厉轻便回到船里,里边狭窄,她躺下缩到一边,等顾珝睡下来的时候,从后面搂住她的腰,和她贴得很近。久违的亲密让两个人都在战栗,厉轻缩着脖子,有些怕,“顾珝……我们能不做吗?我没有生殖腔了,连顾焱都很少碰我了。”
顾珝的手掌揉过她的肩头,抚了抚她的头发,声音沙哑:“大哥是怕了。”
“什么?”
“他怕你连生殖腔都没有,他还是那么想和你做。”
“至少我还是个omega。”
“世界上的omega数不胜数。”他粗糙的手握住她的脖颈,轻轻抚了抚,继续抱着她,“但不是都一样,有一种就是祸害,祸害是很难消,也很难被承认为是美好的,所以人要远离。”
厉轻拉开他的手,艰难转过身去,好去看他的蓝眼睛。他还是伯爵的时候也是蓝色的眼睛,眼里却总是充满了暴躁,如今却沉静如海。
“我是祸害吗……?”她盯着他,“可我觉得你们才是祸害。”
顾珝垂眸,呼吸有些沉,忍耐不住,闭上眼睛吻了吻她的眉心,她皮肤的温度令他亢奋,让他甚至漏出几缕信息素。
他低声承认:“我是,他们我不知道。”
厉轻笑了下,像揽住顾凛的腰一样揽住顾珝,肆无忌惮地把头靠在他胸口,船随着海面微微波荡,她感到无边的抚慰和平静。因为她只是累了,不是爱,不是喜欢,不是任何东西,也就不会有任何负担……
第二天早上,厉轻挣开他的怀抱,跳到海里洗澡,裙子被海浪卷走,她刚想去追,他叫住她。
“别去。”
他有些心虚,总觉得岸上的一切都留不住她,他真害怕有一天厉轻也和自己爱她一样盲目,再也不理会任何人和事。
他跳下海,快速游着,艰难地把她的裙子找了回来,他呛了水,趴在岸边咳嗽,厉轻的尾巴还泡在水里,胳膊撑在沙滩上,不理解地望着他。
“纪丞肯定醒了……你就不想看看他?”他把裙子给她,狼狈说道。
“不是你说,他再也不能来找我了吗?”
顾珝的危机感始终不能消除,“怎么不可能……”
她稍微希冀了一下,又很快目光黯淡了,“见了又怎么样,我有你们就没有他。”
顾珝感觉荒谬,勾勾唇:“这个问题你去问问二哥吧,他可能在帝国的时候就有答案了。”
他拉她上来,她赤身裸体,被他套上湿漉漉的裙子。
“再等等再回去,行不行。”
“不行呢?”
“不行我就把船开慢点。”
厉轻转身回到船里,“那你开慢点吧,我想见顾凛了……”
顾珝自嘲地笑了:“我就知道,你真爱上二哥了……”
-
当船驶回首都城,热闹的景象又回来了,知道顾凛去了一趟帝国,顾珝对她放心好些,厉轻迫不及待地跑上岸去,一抬头就看见顾凛站在不远处,盯着她。
她理理头发,慢悠悠往前走,心慌意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问纪丞的事。靠近了,她主动抱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他反问:“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小怜和珍珠怎么样?”
“你说呢,母亲跟人跑了,他们会怎么样?”
“我……我跟顾珝出来的,没有跑。”厉轻渐渐习惯了顾凛的脾气,自从他们的孩子死了,他就开始变得容易激动。
“你们做了?”
她想了想,点头。
他把脸埋进她脖颈间,轻轻嗅了嗅,“你身上没有他的味道,轻轻骗我。”
她又点点头。
他看着她毫无悔色的脸,把她褶皱的裙子捋好,“我的信息素都用完了吗?”
“嗯,有十多天没有信息素了,我好难受的,顾凛,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把我的症状变得更严重了?那你下次出远门,就再多抽一点血留下,这样提纯出来的信息素才够用……”
“再多抽?再多抽我可能就没命去帝国了,你就没有一天想让我好过吗。”顾凛笑了一下,牵住她的手:“算了……回家。”
“嗯……”
一想起他们死去的孩子,厉轻就发现自己根本不敢问,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顾珝叫住他们,顾凛似乎并不像和他说话,很快地皱了皱眉头。
“哥,是我强迫她跟我出来的。”顾珝解释。
“说这些干什么。”顾凛攥紧了厉轻的手。
“她没什么本事,在顾家跟alpha的关系再不好不能活,帮我和大哥解释一句。”
“你决定大哥会做什么?”
顾珝眯起眼睛,“我只是听说……我“死”的那段时间,她都在地窖里过的。二哥今天很没有耐心,怎么,帝国之旅不顺利了?还是帝国的王子有什么新示下……”
“顾珝。”顾凛严肃地走到他面前,“过两天回家一趟。”
“过两天我要运货,一早和人商量好了的。”
“和厉轻有关。”
顾珝看看厉轻,胸口沉闷,“二哥真的忘得了那种恨吗……”
“当然忘不了。”顾凛木然一瞬,随后转向厉轻,“该回去了,大哥也在找你。”
“好……”
厉轻亲昵地抓着他的手臂,不时抬头和他说话,两人才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相处,他们一齐渐渐远离了顾珝,他逐渐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