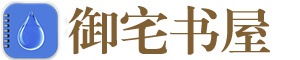半途 第65节
作品:《半途》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过来,承旖没来?”
“得留一个陪妈妈,要不妈妈就疯了。”
呵,这用词,出言不逊。秋辞忍不住揉了下小姑娘的脑袋,没敢真使劲,因为辫子梳得太整齐了,奔波了几百公里都没乱。
“谁给你梳的辫子?”
“妈妈。”忙又补充,“不是我们自己不会,是妈妈嫌我们梳得不好。”
秋辞仔细研究了一下小姑娘的辫子,确实编得有点儿复杂。
他站起身看眼承旗的手机,已经充好电了,拔下来递给承旗。小姑娘们竟然知道她们没身份证不能买火车票,还知道不能在网上约车,会被妈妈查到记录。
“你不怕出租车司机是人贩子吗?或者临时起意要绑架你,找家长要赎金?”
“我上车前给车牌号、司机证件都拍了照,而且全程给承旖发消息。她装病翘课了,在医务室能拿着手机。”
“挺严谨啊,只是没料到百密一疏,手机发消息太频繁给耗没电了,提前充满电的充电宝也给坏了。”
承旗的小脸上露出懊恼又惭愧的表情。
这时席扉端着一盘饺子出来了,秋辞知道他偷懒了,煮的冻饺子,甜品还没做就已经摘了围裙。席扉坐到秋辞旁边,说:“想看你怎么教育小孩儿。”
秋辞又用胳膊肘杵他,让他给承旗留点面子。
承旗饿坏了,吃起饺子就不说话了,两个大人在一旁咬耳朵:“现在的小孩儿真不容易,小学就这么大压力。”“也不是所有小学生都这样吧,我觉得主要是我妈妈的责任。”“你刚才跟孩子说‘百密一疏’,小学生能听懂吗?”“怎么会听不懂?我妹妹可聪明了!刚刚承旗还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和承旖‘有勇无谋’。”
承旗一边吃饺子一边偷觑他俩。
小姑娘第一次来大城市,也是第一次出来“放风”,想看看祖国的首都长什么样。
秋辞替她向妈妈申请,一开始是用的免提,电话那头犹豫半天,问:“让承旗住你那儿吗?你那儿还有多余的房间吗?”
“有,还有一张折叠床,展开了和普通单人床没什么两样。”
可妈妈那边还是犹豫,费了半天劲才问出来:“那徐老师家的孩子这两天会去你那儿吗?”
秋辞听明白了,妈妈是怕自己和席扉两人搞同性恋对承旗产生坏影响。
他立马关掉免提,拿着手机去了另一个房间。席扉坐不住了,怕秋辞他妈又说让秋辞难受的话。
小姑娘眨巴着眼睛看他一会儿,说:“盛哥哥,你去看看我哥哥吧,我怕他跟妈妈吵起来。”
席扉在心里赞了一句:“这孩子果然聪明!”起身追进屋里。
秋辞正一脸严肃地打电话,看见他进来只是抬了下眼皮,又落回去,继续说着:“今天是席扉第一个找到承旗的,是席扉开车带我们回来的,这会儿承旗在吃饺子,也是席扉做的……我们会给承旗什么坏影响呢?妈妈,你别嫌我说话难听,让承旗看看正常的伴侣之间是怎么相处的也挺好的,了解一下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在家里是什么样的,长长见识……以前爸爸是这样,现在刘老师也是这样,孩子丢了才知道关心一下……你希望承旗和承旖心目中的恋爱结婚就是你和刘老师那样吗?你希望两个女孩子长大以后也像你一样因为能干就把一切大包大揽,结婚了也孤立无援,就这么辛苦地过一辈子吗?”
席扉走过去轻轻碰碰秋辞的胳膊。
电话那头像是安静了。席扉低下头把耳朵凑过去,明目张胆地偷听。秋辞本来脸上绷得鼓皮一般,被他闹得松弛了些,重新打开免提。
秋辞的妈妈沉默了很久,说:“你说得有道理……”又过了半天,说:“听你的意思,徐老师家的孩子——”
“席扉,盛席扉。”秋辞纠正妈妈的话,“他叫盛席扉。”
“……嗯,席扉,他人不错,你们过得也不错,我挺高兴的……承旗这次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我很过意不去……但我还是想拜托你们一件事,就是,你们两个,在承旗面前可不可以不要太……秋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承旗毕竟还小……”
秋辞轻轻地翻了个白眼,“妈妈,我开着免提呢,席扉就在旁边听着。”
电话那头顿时又安静了。
席扉忍着笑又碰了碰他,秋辞缓和下语气,“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会注意的。你放心,同性恋绝大多数都是天生的,不传染。”
“嗯,我知道……其实,我最近找了一些书,对那些,稍微了解了一些……”
秋辞脸上显出动容。
“秋辞,妈妈想问问你,你是天生的吗?还是……因为你初中那件事——”
“不说这个了。”秋辞再次打断母亲,语气比之前都硬,“不提那些事了。”
电话里又沉默许久,妈妈问出最后一句:“秋辞,你怨我和你爸爸吗?”
这是汉语唯一的欠缺,说得太简略就会丢了时态。
是曾经怨过吗?还是依然在怨呢?
“别想这个了,妈妈,都已经过去了。”秋辞回以严谨的完成时。
之后秋辞请了假,席扉也给自己批了两天假,次日一早带着承旗去看升旗仪式,之后又游了颐和园。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带承旗去爬长城,但是妈妈那边实在是受不了了,不停地打电话发消息来问,让秋辞有点儿吃不消。最重要的是承旗也想家了,想承旖,想妈妈,承旖也想她。
他们没让妈妈来接,自己开车把承旗送回去。秋辞看着妹妹承旗一路欢笑地和妹妹承旖拥抱到一起,妈妈左手一个右手一手揽住她们,让他不由微微湿了眼眶。
妈妈和刘老师请他们进屋坐,秋辞推却了,说还要去席扉父亲那边看看。他冲依依不舍的承旗和承旖摆摆手,转身和席扉一起离开了。
第109章 全文完
(73章前面添了一部分,和这章有一丢丢关系,可以清缓存看。)
两人在席扉父亲那边吃过晚饭才走,城市已经点起灯。
席扉和那些匆忙往家赶的司机不同,他开车开得包容谦让,还能腾出时间往右看一眼:秋辞微微偏着脑袋仰靠在椅背上,眼神带着饭后的餍足,街边招牌的彩光和前方车尾灯的红光在他脸上轮番上色,却染不透他净白的脸。
秋辞惯有这种局外人气质,不是因为他冷漠,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感情过于充沛,需要用克制以自保,防止过度的激情将他燃尽。
席扉知道自己是少有的、甚至是仅有的那个能看到澎湃的激情从秋辞静物般的躯体中迸发出来的人。秋辞对两个妹妹说话都要藏起五成以上的温柔,只有席扉被秋辞百分百温柔以待。
席扉问过秋辞,羡慕妹妹们吗?
秋辞想吃脆皮鲜奶,所以当然是羡慕。所以潜台词是:“嫉妒吗?”
秋辞说他不嫉妒。妈妈曾经是失败的妈妈,而他已经确凿是个失败的孩子。现在有承旗和承旖帮助妈妈,母亲和孩子相互监督敦促、共同进步,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好的结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有两样半不由秋辞自己做主,所以不嫉妒。
秋辞给席扉讲自己妈妈生长于一个怎样冷漠的家庭,姥爷在省会上班,薪酬优厚,妈妈考上省会的大学,周末找姥爷要生活费,二十公里的路,大巴车票要两块,姥爷给她十一块。十块钱是生活费,一块钱是十公里的车票钱,剩下十公里要妈妈自己走回去。
所以妈妈这辈子咬牙切齿要做一名优秀的母亲,可她不会,只是笨拙地学。
所以秋辞不怪她第一场实验失败了,人很难一下子就掌握自己没见过的东西。
他只惆怅这绵延不绝的因果。
一切都有缘由,连徐东霞都有缘由。因为她生在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因为她是长女,因为……这是秋辞最恨这世界的地方,连作恶者都有缘由,而被害者却可以无缘无故被害。
因为曾经被父母家暴,所以长大后把巴掌挥向自己的孩子;因为幼时被鸡奸,所以长大后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另一个孩子;因为同组学长不好,所以就对新来的学弟不好;因为今天上司吆五喝六,所以下班去吃饭时也对服务员挑三拣四。
秋辞很高兴自己跳出了这个“恶”的传递链,他逃出了这种命运。
他不仅仅是受害者,也是幸存者,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成为徐东霞的“恶”的继承者。徐东霞曾经施加在他身上的那些恶将从此失传,永绝于这个世界,他和徐东霞彻彻底底地分道扬镳。
他请席扉做好准备,因为他要点评徐东霞了:“被大他者彻底操控的失语者,一言一行都是执行大他者的命令,甚至由大他者的奴隶变为其帮凶。”
席扉无奈苦笑,虚心地请秋辞讲下去。
“你要庆幸你是一个男孩儿,你之前的那些幸福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秋辞言简意赅,把席扉也剖开了,“如果你生来是个女孩儿,你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徐东霞……当然也可能不会,你有一个那么好的爸爸,但总归不能那么幸福。”
席扉舌底有些发苦,无奈他这么心狠。可是秋辞自我剖开时毫不手软,如今他也这样剖自己,是因为他不再把自己当成外人。
“大他者一定是坏的吗?”席扉问。
秋辞顿时语塞。
“如果完全没有大他者,人是什么?”
“动物。”秋辞很快就有了答案。
席扉满意地点头,“我认为人是动物本能与大他者的交集。本能是有好有坏的,大他者也是有好有坏的。本能会与大他者打架,也会和大他者合作,你以前讲的本我和自我也是同样。所有这些都不是电影里的正派和反派,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
秋辞赞叹地看着席扉,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果然只有席扉能产生如此想法:人身体里面那只永不满足的动物都可以是好的,外面那个喋喋不休的大他者也可以是好的。
秋辞始终为一个念头感到困顿:人是被扭曲的动物,动物的原欲与想要成为人的自我要求必将永远纠缠撕扯。所以拉康认定所有人都疯了,所以秋辞认定人活着必然受罪。
而席扉说人是动物与大他者的交集。交集意味着重叠。也许这就是人活着的任务:去管理这片重叠区域,让它们平衡、调和,并且避免一方完全征服另一方;成为一个既非动物又非大他者奴仆的真正的人。有了任务,便不再是虚无,不再是无意义。
“所以是不是天生的同性恋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性取向是纯动物性的,而人是在交集里进化了很多年的人。”席扉有些狡黠地说。
秋辞又惊讶了,没想到他会落到这里。原来刚刚又是起兴,人生的终极哲理都只是借用,只为解开秋辞心里的惑。
“你特别介意这个,是吗,秋辞?你介意自己可能‘本来’不是同性恋。你喜欢寻求答案,但是生活可太tm的狗日了,越是对人影响大的事好像就越没有复盘的必要,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没有重现的机会。对那种只会发生一次的事,你永远都没法通过第二次去验证你的猜想,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秋辞一直扭头看着他,惊叹一个人竟能对另一个人熟悉到这种程度。
席扉也转头看了他一眼,柔和地笑着:“我以前说,我会记着你说的话,积累得多了,总能理解你。我那不是随便说说哄你高兴的。”
秋辞的眼睛不由微微地睁大了。
他这么近地看着席扉的侧脸,却能同时如远望高山流水般,瞬间抓住席扉的全貌。而他闭上眼睛,看不见席扉了,脑海里却清楚地理出席扉的眉毛是怎样一根根地趴在那双眼睛上方,唇上的细纹又是如何在笑时展开来,在为难时聚拢住。
他原以为允许一个人走进自己心里是把两个人都关进封口的袋子,而眼前实则是天高海阔。
“你还介意我不是天生的同性恋,是吗?”
秋辞笑了,轻轻地歪了下头,就像刚刚席扉做出的洗耳恭听的样子。
“首先,性取向的定义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你同意吗?”席扉车开得很认真,同时说得如此熟练,可见排练多时了。
秋辞笑着点头,“同意。”
“其次,‘性觉醒以后性取向就不可改变了’,这种理论也是值得商榷的,你同意吗?”
“……同意。”
“再次,你说性向的倒错都是暂时的,等到新鲜劲儿过去了,荷尔蒙恢复正常,性取向就也会恢复‘正常’。但是我觉得你说得不对,我觉得我们俩那么和谐,新鲜劲儿永远都不会过去的。那些高x和快感不是白给的,它们是我们的共同记忆,身体的记忆是,脑子里的记忆也是。记忆难道不是人重要的东西吗?我现在一想那种事,唯一想到的就是和你,你看我现在说着和你这个那个就又有反应了,你还敢小瞧那些记忆的威力?”
秋辞哈哈大笑,让他好好开车。
可席扉还没说完,“没有什么定论,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别拿定论套活人。你看我以前一点儿不懂绳子,现在不也变得挺喜欢?因为捆住你,你就不会再乱跑了,因为绳子能在你身上印出花纹,好看得很,因为捆你的时候你越安静,之后就越兴奋,我就喜欢得不得了。会失去新鲜劲儿吗?我觉得不会。秋辞起码能有36种捆法吧?一种捆法我起码得玩儿上十次才觉得过瘾,离玩儿烦还早得很,何况之后还可以两种捆法相结合,就是a(36,2)——”
“c(36,2)。”
席扉一脸神秘地看过来,“相信我,是a(36,2),先后顺序不一样,你的反应也不一样。a(36,2)是多少?之后还可以有a(36,3),(36,4),我现在不担心玩儿法不够用了,我现在担心咱们玩儿不到那个岁数。”
秋辞笑得全身直颤,说他老是冷不丁就不正经。
“那么正经干嘛呢,有时正经,有时玩儿闹,这多好。秋辞——那天为什么愿意给我用嘴?”
他突然就正经了,问这种问题。
“你问过,我回答你了。”
席扉一副将他看破的表情,“回答得这么快,那当时肯定是骗我了。”
秋辞眼帘垂下来了,牙齿舌头在嘴里预备半天,说:“我想拿你做脱敏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