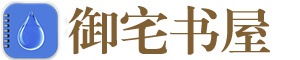第117章
作品:《岛屿沉沦日》 作为补偿,全国各地,她可以任选一处落脚。兰姨会为她购置房产,并额外开给她一张七位数的支票保障生活。
“现在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面对始终保持缄默的薛媛,兰姨轻轻推来杯盏,像递出答题卡。
在气场全开的兰姨面前,薛媛实在像张白纸。
囫囵饮下一口清苦,发紧的喉咙终于漾出干涩的回应:
“是祝叔让你来的吗?”
“不,是我单方面的意见。你父亲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
兰姨摇头,神情淡然。
“但这个家要维持安宁,总要有人来做恶人不是吗?所以你有怨气的话,现在可以直接撒给我,不必憋在心里或苛责你父亲。”
……
其实这样乘胜追击,速战速决的场景,兰景莼早已预想过无数次。但让薛媛有气都冲着自己撒这一环,来得实属临时。
两小时前,她走进气氛凝重的主卧,安抚发怒的丈夫。将手搭在他肩上,装腔作势地哄:“孩子的话,听听就得,那么较真干什么……”
丈夫没有任何回应,只将脸埋在掌中,良久,才从指缝里溢出一句粗粝的:
“你出去吧,让我自己休息会。”
伴随声音,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电光石火间,兰景莼意识到,丈夫在哭。
认识这些年还是头一回。
他真真正正地在伤心,喉结抖得停不下来。
虽然赶走薛媛对兰景莼来说势在必行,但能有今天这么一边倒的顺利局面,也实属意外。意外到竟然生不出胜利的喜悦。
后来开车时兰景莼脑中数度闪回丈夫的颓唐。
心像被凿开一块。空落落透着风。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触了。
但计划仍得推进。
具象的利益永远高于虚幻的恻隐。
谈话地点选在她名下的第一间不动产。
一栋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楼茶舍。
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如同她人生的缩影。
从穷丫头到人上人,兰景莼不会忘记过去的自己付出多少努力,跌了多少跤,卖了多少笑,又死皮赖脸吃过多少闭门羹。
总之是混出来了,现在整个兰家几乎都背在她背上。
她是光宗耀祖的负鼠。
烂鸡窝里的金凤凰。
如果兰家还有族谱,她势必单开一页。毕竟目前而言家里没有人话事权能大过她了,所有人都倚着她,服从她,为了跃龙门,向上爬。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真的很累啊。
前些日子费了很大功夫才把兰景益保下来,只从集团赶走,不追究法律责任。
可如此结果仍难为家人所接受。
母亲托着她肩膀抹垂泪,说小益是不争气,可小益也是为了帮你啊,公司里情况那么复杂,你怎么着也得留点自己人傍身,想想办法,得给小益再安排个别的差事啊。
能想什么办法。
她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一团乱麻。
自房市开始崩盘,祝家就接连磋磨不断。
在建项目烂尾,贷款逾期,子公司破产清算,投资接连失利……为了确保未来儿子们的好日子,兰景莼必须趁着自己还精明强干时,打起十二分精神去抢食。
她把这视作母性的本能。
到今天她已经做不了世俗意义上的好人,但至少还能做个孩子们眼里的好妈妈。
所以薛媛的存在对她而言只是麻烦。
一个从天而降的既得利益者。
往日里连个笑脸都懒得施舍,祝国行却巴巴地纵容着,规划着要怎么弥补,将她领回家来好好养着。
老实说恶心透了。
当然兰景莼本人很明白,这种恶心来源于别扭的嫉妒。
她一直都很嫉妒那些能出生在好家庭里的人,嫉妒她们有血缘这颠扑不破的纽带,来为她们输送财富。不用拼不用抢,就可以坐享其成。
直到今天,她从祝国行的眼泪中品味出对等的……不幸来。
如果没有这层血缘,痛苦不会被推到这样的高度;如果没有那些财富,他们也不必抉择取舍,只需享受失而复得。
在身不由己名利场中,人人都是被欲望和权利异化,咬紧牙关的斗兽。
难得的悲天悯人。兰景莼自嘲。
所以就让薛媛骂骂吧,让她发泄一下,让她能够轻松,哪怕一丁点儿——
“我可以离开西洲。”
茶杯被放下,再度开口的女孩并没有作出任何撒气的举动,而是看向她,用不悲不喜的语调同她商量起支票打款,以及房屋折现的价格。
像一潭死水,荡不起任何波澜。
除了达成共识后的额外补充:
“在这基础上,我还需要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动祝合景,能让他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一条兰景莼甚至都没觉得有分量上谈判桌的条款,被她讲得严肃慎重。
得到应允后,如释重负地露出微笑。伸出左手在空中挥了挥,安静地离去。
这算什么?
四周回归寂静,兰景莼看着那扇合拢不动的门,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从今天开始才真正认识了薛媛这个人。
第104章 .仍然怀念我们有过
室外阳光正盛。
碧蓝色的天幕清朗如洗,大片流云被烧灼,金色的光晕。如果不是从车窗缝隙里挤进来的风冷冽得像刀片,道道割脸,薛媛都快忽略,西洲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冬天。
这是薛媛来西洲的第三个冬天。
从四十米老破小到合租公寓,从云川到文和盛世。她住过许多地方,搬过好几次家,到头仍然是只无法落地的鸟。
等待兰姨筹备现金大概需要一月左右。
倒长不短的时间,薛媛不打算再回去云川,接下来不过是找张床睡觉,不如直接到花店附近找间商务酒店,之后要离开也方便。
手机里有裴弋山发来的信息,大致是告诉她,会借昨日之事同祝国行协谈,尽可能顺水推舟,让他们的关系由地下转至地上。
大有趁热打铁,一鼓作气结婚的架势。
说来讽刺。
在祝国行竭力反对时,薛媛还相信她和裴雨山只要齐心协力,不放弃,熬下去就可以。
而确定离开祝家后,一切变了。
故作轻松回复过对方:【我这边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最近还是稍稍避嫌吧。等风头过去再联络】后,她开始思考的是如何与对方割席。
过去二十四小时听来的种种言论如此刻凛风不断渗进薛媛耳畔,组合成一句魔咒般的卮言——
糟糕透了,裴弋山简直疯了。为一个不三不四、品行不端的培训班预制情妇,心甘情愿当凯子,肤浅又蠢钝,天大笑话。
指腹紧紧摁住右手的铂金戒托,钻石挤压皮肉,生硬的触感,留下暗红色的印窝。
薛媛前所未有通透,前所未有迷茫。
……
下午一点半,花店正补货。
穿围裙的妹妹把冷藏柜里的鲜切花分批抱出,按品类一一填进铁艺的展示架。几只溜圆的蜜蜂绕着她飞,她缩脖子,腾不出手所以谨慎地左右躲。
转头瞥见拖着行李箱而来的薛媛,像块回弹的海绵,整个人连同表情一下舒展开了:
“媛媛姐!我以为你今天不来呢!”
是又有几天没来了。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咸鱼老板,简直没有一点点自食其力的自觉。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男人,名下唯一的产业靠尽职尽责的店员。薛媛很惭愧,强颜欢笑将行李推进收银台放好,系上围裙,搭手投入劳作。没几分钟,被妹妹霸道地抢过手里花束,推搡到一旁太师椅上坐下。
“你休息!”
妹妹说,非常严肃。
“你本来身体也不好,最近又降温,流感盛行,千万不要累着了。”
店里没有镜子,薛媛通过妹妹的反应判断自己看起来十分憔悴。果不其然,妹妹碎碎念中一本正经提到给她补身体:
“我外婆家的老母鸡差不多要出笼啦!赶明儿我去给你弄一只,你找人杀啦,再拣点中药材一并炖了吃,大补,纯天然无公害!”
“啊真不用。”
薛媛连连摆手,用家里装修暂住酒店为由,婉拒妹妹的好意。
“噢。所以你拎着行李箱?”
妹妹回过味来,下意识脱口:
“装修啊?那小景也出来了住吗?怎么没听他提起这事……”
这就是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坏处了,撒谎不再方便。薛媛忽然意识到自己几乎没对妹妹说过半句实话,不由得心生愧疚。
真假掺半,解释起自己因同父母关系不融洽而独自居住的实情。妹妹大概是从她语气中辨别出话题太隐私,反倒不好意思地道歉:“哎呀我太多嘴了。”
顺便亡羊补牢,热情邀请薛媛去自己家里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