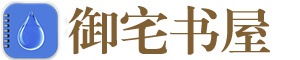七零之农学大佬 第59节
作品:《七零之农学大佬》 第59章
第二天, 北疆的天空依旧是那种澄澈无云的湛蓝。
林听淮、一名叫小赵的年轻技术员,以及苏承许和他带领的两名熟悉地形的战士,乘坐着吉普车, 带着处理好的少量种子和简单工具,前往西边的盐碱滩。
所谓盐碱滩, 地势低洼, 地表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盐霜, 土壤板结黏重,踩上去硬邦邦的,裂缝纵横。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涩的气味,只有极少数叶片肥厚、根系发达的盐生植物在地上稀稀拉拉地生长着。
看着眼前盐碱滩地里的景象,刚走到地前的林听淮也不由沉默了。
他们在盐碱滩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选择了一小块相对平整、盐渍化程度具有代表性的地块。
和林听淮想象中的一样,在盐碱地…尤其是如此具有代表性的地块种植,过程极其艰难。
铁锹挖下去,十分费力。铁锹的刃口楔入灰白色地表,发出的不是泥土被翻开的“嚓嚓”声, 而是一种近乎金属摩擦的、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苏承许第一个动手,他双臂肌肉贲起, 军装袖子挽到手肘, 将全身重量压上锹柄,铁锹却只没入寸许,撬起的不是松软的土块,而是一大坨边缘锋利、夹杂着白色结晶、坚硬如粗陶片似的板结土。
这土块沉重异常, 摔在地上竟发出“砰”的一声闷响,碎裂开的断面闪烁着盐霜的冷光。
“好家伙,这地跟铁板似的!”旁边一名战士试了试, 咋舌道。
林听淮蹲下身,用手指捻了捻碎土,指尖立刻沾上一层滑腻的咸涩粉末,土壤颗粒粗粝,毫无黏性。
“盐分太高,胶结严重,直接播种不行,种子很难顶开。”她蹙眉道,目光扫过带来的几个水壶和两个备用铁桶,“得先软化表层。”
办法原始而费力,小赵技术员提着水壶,小心地在选定的小坑位置浇上少量水。
水迅速被/干燥的盐碱土贪婪地吸吮进去,只留下深色的湿痕,但却并未立即软化土壤,而是需要等待。
他们只能轮流作业,一人浇水浸润,等待几分钟后,另一人再用铁锹或镐头,对着那点湿痕奋力挖掘。
即使已经经过浸润,土壤依然十分顽固,每一次下镐都震得虎口发麻,撬起的土块虽不那么坚硬如石,却也像潮湿的石膏块,沉重而黏结。
林听淮在一边也拿起一把小铲,试图清理坑底的碎土和盐结皮,她虽然力气比不过男同志们,但动作却更细致,铲刃刮过坑壁,带下片片灰白盐壳,露出下面颜色稍深、但仍布满盐丝的内层土壤。
空气里咸涩的味道更浓了,混合着汗水的气息。
“坑不用太深,这种地方深了反而容易积水返盐,闷坏种子。”她一边清理,一边对负责挖坑的大刘说。
“主要是把表层最硬、盐最重的结皮去掉,给种子一个稍微柔和些的发芽环境。”
苏承许默不作声地听着,手下动作调整,将原本打算挖深尺许的坑,控制在半尺左右,且坑底尽量平整,避免洼陷。
每挖好一个坑,他们就立刻将精心准备的耐盐-2号以及几粒混选-3号种子,小心翼翼地放入坑底,每坑只放两三粒,并严格间隔开。
将种子放入挖好的坑里后,覆土则是另一个关键。
种子的覆土绝不能直接用挖出来的、盐碱极重的原土,而是用他们从试验站苗圃带来的、相对肥沃疏松的客土。这是林听淮坚持要带的,为了这些土她甚至减少了部分工具的携带量。
林听淮亲手捧起一把客土,客土整体呈深褐色的,带着些许腐殖质的微润感。
她将其均匀撒在种子之上,厚度仅能勉强盖住种子,薄薄的一层,如同一个短暂的缓冲区和微型的保育室,能在种子萌发最脆弱的阶段,提供相对较低的盐分环境和更好的水分条件。
“覆土一定要轻,不能压实。”她示范着,用指尖将土轻轻拨拢,“压实了透气差,种子不易出苗。”
每一个坑都重复着这样费力而精细的过程:艰难破开盐壳、等待浸润、浅挖、点种、轻覆客土。
汗水不断从额头滚落,滴在灰白的地面上,瞬间被吸收蒸发,军装和工装的后背早已被汗浸透,紧贴在皮肤上,又□□燥的风吹得半硬。
太阳越升越高,无情地炙烤着这片银白的世界。
盐碱滩反射着刺目的光,晃得人眼睛发花,偶尔刮过的风也带着咸热的气息,扑在脸上,很快就把皮肤上的汗液吹干,留下一层细细的盐粒,微微刺痛。
当最后一粒种子被那层宝贵的客土轻轻掩埋,在这片几乎被生命抛弃的盐碱滩上,几十个不起眼的小小土包悄然出现。
它们与周围茫茫的灰白相比,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滑稽,但蹲在旁边的四个人,望着这些小小凸起,疲惫的脸上却露出了如释重负又充满期待的神情。
林听淮直起酸痛的腰,用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望向这片刚刚被驯服了一小角的白地。
“好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浇水定根,然后…就看它们自己的了。”
苏承许提起所剩不多的水桶,将最后一点清水,极其节约地、均匀地淋在每个种植坑上。
水迅速渗入那层薄薄的客土,消失在灰白的地表之下。
完成这一小片盐碱地的播种,已是日上三竿。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手上磨出了水泡,军装和工装上沾满了灰白的盐渍。
稍作休整,啃了几口干粮后,他们并没有多做停留,而是立刻出发,前往更北面的沙化地。
前往沙化地途中的路途崎岖无比,吉普车在几乎没有路的戈壁滩和丘陵间颠簸前行,卷起漫天黄尘。
他们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而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望无际的、连绵起伏的沙丘和沙地,植被覆盖率极低,只有一些低矮的、叶片退化的沙生植物在风中摇曳,土壤完全是松散的沙质,毫无保水保肥能力。
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热浪蒸腾。
看着眼前这大片的沙地,在摸摸自己酸痛的腰,一行人一时间也有些“绝望”,但一鼓作气,再而…闭着眼睛加油干吧,他们简单的给自己鼓下劲儿后,便开始动身寻找合适的种植点。
然而…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沙地上,寻找合适的种植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沙地一望无际,地形随着风势时时微变,脚下是流动的细沙,走一步陷半步,苏承许走在最前面,用一根长木棍探路,寻找着沙层较薄、可能蕴含一丝生机的地方。
磕磕绊绊找了半小时后,终于,在一道背风的沙梁后侧,苏承许发现了一片地势略低、沙面相对板结的区域。
“这里。”他用木棍戳了戳地面,沙层下传来不甚清脆的“噗”声,不像别处纯粹松软的“沙沙”声。
林听淮赶过来,蹲下身,用手扒开表层滚烫的浮沙,约莫扒下去一掌深,指尖触到了些许不同,沙粒变得略微湿润,且混杂了零星深色的、极细的黏土颗粒。
“就这里吧。”她拍掉手上的沙,声音因为干渴而低哑,“背风能减少幼苗被吹走或沙埋,下面有点黏土,或许能存住一点点水。”
确定了地点,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在流沙上挖坑几乎是一种与自然法则对抗的玩笑,铁锹铲下去,松散的沙粒立刻从两侧滑落回坑里,根本形成不了坑壁。
“这样不行。”苏承许停下动作,皱眉看着不断回填的沙窝,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沙梁上那些枯死已久、根系却还顽强扎在深处的红柳残枝和几丛干硬的骆驼刺上。
“或许..我们需要一些围挡才行。”话音刚落,他便带着两名战士去搜集那些坚韧的枯枝和带有硬刺的灌木条。
林听淮和小赵则用铁锹和双手,尽量将选定点位的浮沙清开,露出下面稍密实的沙层。
苏承许将他们搜集来的枝条,用力插进清开区域的边缘,紧密地排成一圈,形成一个个直径约一尺、深约一尺半的简易围挡。
枝条的下端尽可能深插,上端露出地面半尺有余,虽然这粗糙的围栏无法完全阻挡细沙,但至少能减缓流沙回填的速度,为种植争取一点时间。
解决了沙子回填的问题后,坑的深度也是关键。林听淮要求他们种植的坑要挖到触及那层略带湿气的、含有黏土颗粒的沙层为止。
“深坑可以聚集夜间可能的少量露水,也能让根系尽可能向下寻找水分。”她解释道,自己也拿着小铲,跪在沙地上,不顾沙粒滚烫,一点一点掏挖坑底的沙土。
挖好坑,小赵打开一个布袋,里面是从团部马厩旁收集来的、铡得极碎的干苜蓿草屑和少量腐败的落叶,这些东西在别处或许不起眼,在这里却是珍贵的保湿材料。
林听淮抓了一把草屑,均匀地铺在坑底,厚度约两指。
“别铺太厚,太厚了容易腐烂发热,反而伤根。主要是隔开下面的冷沙,保持种子周围微环境的湿度。”她细致地将草屑摊平,又撒上极薄的一层客土,防止种子直接接触可能发酵的草屑。
抗旱-1号的种子经过特殊处理,显得略有些粗粝,林听淮用指尖捏起种子,微微颤抖着,但不是因为紧张,而是长时间的暴晒和劳累。
她屏住呼吸,将种子轻轻点在铺好客土的坑底中心,每坑三到五粒,呈梅花状分布。
“浅播。”她强调,随即用指尖从旁边拢来极细、极干燥的浮沙,像筛粉一样,极轻极薄地撒在种子之上。
覆盖的沙层薄得几乎能看清下面种子的轮廓。“沙地导热快,白天表层温度极高,深播会灼伤种子或闷死嫩芽。浅播利用表层沙昼夜温差大、夜间可能凝结露水的特点,只要能顶出沙面,就有希望。”
覆沙后,他们又将之前挖出的、稍微湿润一点的深层沙土回填到坑里,填到距离坑口约三寸处停止,然后在坑口表面,又撒上一层更干燥的浮沙,形成一个浅浅的凹面。
“凹面能承接可能的微量降水或露水。”林听淮做完最后一个坑,已是气喘吁吁,脸颊被晒得通红发烫,嘴唇干裂起皮。
她看着这一排排被粗糙枝条围护着、表面不起眼的小小沙坑,眼神专注得像在完成最精密的实验。
苏承许提起最后半桶水,用一只旧搪瓷缸舀起,小心地沿着每个坑的内壁缓缓淋下,让水慢慢渗入深层的沙土和保水草屑中,避免冲走表层浅覆的种子。
水迅速□□渴的沙地吞噬,只在坑壁留下深色的湿痕,很快又被蒸发带走大部分。做完这一切,四个人都近乎虚脱,瘫坐在滚烫的沙地上,背靠着吉普车投下的一小片可怜阴影。
“能活下来多少,就看它们自己的造化了。”林听淮蹲在地上,轻轻抚摸着沙土表面,低声说。
回程的路上,吉普车里很安静,大家都累得说不出话。
林听淮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速掠向后的、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戈壁景象,感受着身体极度的疲惫,心里却异常踏实和平静。
种子播下后的日子,时间在每日固定的观测记录中缓慢流逝。
实验田里,经过预处理的“抗旱-1号”、“耐盐-2号”、“混选-3号”以及作为对照的本地常规品种丰稳-8号,都陆陆续续顶破了土层,展露出鲜嫩的绿意。
幼苗的长势,在初期令人欣喜。尤其是实验品种,在研究人员规范的管理下,株型整齐,叶片舒展,绿油油地立在划分整齐的小区里,与旁边兵团战士们粗放管理的大田作物相比,显得格外精神。
附近的村民和兵团职工,劳作之余,总喜欢绕到实验田这边来看几眼。
起初是纯粹的好奇,后来看到这些种子长得确实不赖,眼神里便多了几分羡慕和探究。他们自己的地里,种的是本地种植、稳定性高的丰稳-8号。
今年开春风调雨顺了一阵,地里的丰稳-8号也是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看起来并不比那些实验田的苗子差。
甚至有老农蹲在田埂上,吧嗒着旱烟袋,用带着浓厚乡音的话说:“瞧这架势,咱这丰稳也不差嘛!专家鼓捣的那些,好看是好看,也不知道结不结实?”
这种议论,林听淮和张广林他们听到了,也只是笑笑,并不多做解释。
时间在精心的记录中过的飞快,转眼就进入了六月,北疆的夏天真正露出了它严酷的面容。
太阳一天比一天毒辣,像悬挂在头顶的白炽火球,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风也不再是春日里带着寒意的清冽,而是变成了干燥灼热的火风,卷着地上的沙尘,抽打在植物叶片上,发出簌簌的声响。
雨,成了最稀缺的珍宝。
起初,只是半个月没下雨,这在北疆的夏季并不算特别异常。
老辈人常说“春雨贵如油,夏雨要靠求”,靠天吃饭的农人早已习惯了与干旱周旋。
村民们虽然开始有些担忧,田里的灌溉频率增加,但还能维持。水渠里的水日渐减少,机井需要更深的抽取,但总归还有水,只要一场雨下下来就能缓解现状。
实验田这边,因为有严格的用水计划和苏承许协调来的优先保障,加上种植密度较低,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林听淮每日记录的气象数据和土壤数据,曲线开始呈现出令人不安的下降趋势。
她提醒张广林和孟祥瑞,也通过苏承许向团部做了旱情预警,但面对广袤的土地和有限的水源,预警能做的也仅仅是提醒大家更加节约用水。
当“一个月未降一滴雨”成为现实时,轻松的氛围荡然无存。
恐慌,像滴入滚烫沙地的水,迅速蒸发弥漫在空气中,却又以更沉重的压力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戈壁滩上的蒸发量远远大于任何可能的补给,河流水位骤降,近乎断流,许多浅层机井开始抽不上水,或者出水浑浊含沙,深井的水位也在持续下降,抽水时间越来越长,出水量却越来越少。
灌溉成了奢望,基础用水保障都开始紧张。
最先显现出危机的是大田作物,由于缺乏足够的水分补给,又遭遇持续的高温炙烤和干热风侵袭,丰稳-8号原本油绿的叶片开始失去光泽,边缘卷曲,颜色由绿转灰,再变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