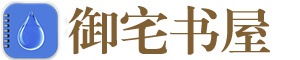替身仙子想回家放牛 第91节
作品:《替身仙子想回家放牛》 短短十日,清徽道院凡间各处的分院不是被打、砸、抢,烧一空,就是被雪家的羽客道士们贴了封条,永无解封之日。
再过段日子,就会有新的道观在原址上重建,或许都不用建,重新刷个漆,换块牌匾,选个良辰吉日放串炮仗便可重新开观。
清徽院总院,内外门弟子有的选择投靠修界其他仙门道观,有的则选择脱下道袍回归尘世。也是走的走,散的散。
柳陌始终不曾露面,华清作为他的大弟子,几次出面支持大局,也于事无补。
他总不能敲锣打鼓、哭天喊地求他们留下来。
最后华清也累了,走吧,都走吧。
清徽道院当初崛起得有多快,现在覆灭得就有多快。柳陌知道她会报复,也猜想过她会选择何种方式。
这次完全在他意料之外,或者说他低估了流言传播的速度和可怕之处。
这让他沉寂了许久的心又开始泛起涟漪,这才是他想要的势均力敌。
果然这世上,除了她,谁都不行,没有人可以替代她。
华清寻来时,柳陌正坐在树下看书,外面发生的事,对他好像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他长发未束,着一身宽大的藏蓝道袍,赤足半卧在树下软榻,身边陪侍了一名红衣青年。
这青年华清也是第一次见,他目视前方,一动不动,颇有些古怪,华清不由多看了几眼。只是柳陌不介绍,他也不好多问,上来规矩行了个礼,“师尊。”
柳陌微微一掀眼,他的容貌还十分年轻,双眸黑沉,似藏有无边暗涌,随意地一瞥便让人不寒而栗。
“你为何不走?”柳陌问。
华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柳陌面前,所有的小心思都是藏不住的,华清之所以能成为他首徒,得他亲授,就是因为他大多数时候心里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想。
给他指一条路,他便直直地往前走,风雨也不回头。
有两种人可以走得很远,一种是华清这样的呆子,另一种柳陌认为是自己,谋定而后动,每一步都经过精准计算。他们都是一条道走到黑。
现在,他的路也走到尽头了。
华清干脆在榻边跪下,“我为师尊烹茶。”
柳陌翻了一页书,没搭理他。
不多时,就有讨伐柳陌的正义之师上门,前殿无人,他们畅快打砸一通,得意忘了形,又嚷嚷着要把柳陌揪出来,按头谢罪,风风火火直闯后苑。
这处院子便是从前长有月华树的小破观前院。清徽道院往外扩建后,被单独圈出来,囊括在柳陌寝殿庭院范围内,平日里,只有华清可随意出入,来扫扫院、浇浇水。
院外喧哗声近,柳陌不悦地蹙眉,华清已起身拔剑迎去。
不过是些不值一提的无名之辈,想趁乱捞些好处,又听闻柳陌修为高深,已在山下徘徊数日。
这日见清徽院弟子都走了个干净,终于鼓足勇气上山,一路畅通无阻更助长他们气焰,以为柳陌不过空有虚名,此时透过圆形的月洞门,见树下侧卧一名慵懒青年,当即叫骂开。
“柳陌,你这王八犊子,还有心思睡觉?!”
“你看,他优哉游哉,还在看书喝茶。”
“做下那么多恶事,竟还如此心安理得,真是该死。”
“柳陌,你……”
这人话音未落,华清一剑刺去,他只得后退躲避,二人当即缠斗在一处。
其余人各自分成两拨,一拨围殴华清,一拨朝着小院大步走去,刀剑、法器俱都出匣。
“聒噪。”
柳陌右手一抬,树下枯叶片片竖起,浮在半空,他指尖微挑,叶片激射而出,众人挥剑抵挡,叶片触之即碎。
一片裂作百片、千片,如针似芒,锐势却不减,呈弧状围杀。叶针纵横穿梭,不过三五息,场中人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已被刺成了网筛,血肉模糊,兵器铿铮落地。
华清持剑呆立在原地,柳陌挥挥袍袖,“你这些年也攒了不少积蓄,下山去涧泉斋,找雪光遥开张公文,花点钱就能买下一间道观。去金庭山吧,那是块福地,以后自己做观主,别再跟人说,我是你师尊。”
华清抬起头,柳陌再一挥袖,他眼前一花,站定时,已被他送到山下。
原地矗立良久,华清收起佩剑,跪地朝着清徽院三清殿方向,结结实实磕了三个头,起身大步离去。
院中柳陌自一盏莲灯中捻出一缕金芒,注入身侧那红衣青年额心,一直呆坐的青年瞬间活了过来,转动眼珠,挺了挺背,看向柳陌。
“去吧,我总得准备些回礼。”
红衣青年两手结印,身形随即化作烟雾消散。
柳陌端起茶盏,往天上一泼,水镜随即显现,镜中山石花木、朱门拱檐,都是他所熟悉的。
红衣青年出山门,御剑腾空,柳陌便看见云下高山起伏,河流蜿蜒,城镇屋舍俨然。
*
龙凤镇,临水的窄街上搭了青灰色布棚,棚下摆满桌椅,两三人围坐桌边,有的打牌,有的下棋。
女人们在河埠头洗菜,男人撑船停靠在岸边,将大筐的蔬果肉类卸下,孩子们举着棒糖呜啦啦跑过,身后还跟了只大黄狗。
历来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红白喜事都直接摆在大街上,早中晚三顿,若是白事,守夜人还有宵夜吃。
红事一般是三天,白事七天,要做法事。
邻里们都可以来帮忙,除了掌勺的大厨是从酒楼里请来,其余洗菜、蒸饭、洗碗,都是邻居们。
每家交上一点份子钱,一家老小都能来吃,平时吃得简单,家常菜,最后一天的晚饭才是正餐。
不过境元先生最近挣了大钱,还白得了一套房子,礼金收得不多,顿顿都是正餐,邻里们都夸他大方。
衔玉他们来早了一天,现三人围坐在土漆刷的黑桌边,由新媳妇手把手指导,学习打麻将。
学了一上午,柳催雪、衔玉,阮芽都学会了(按智商排名),苗苗心思一转,“那就开始吧,要打钱哦!”
“打钱打钱!”衔玉摩拳擦掌,迫不及待。
阮芽还没完全搞懂,专注理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条戒尺,把每一块牌用戒尺整整齐齐列成直线,玩起了叠高高。
柳催雪开始进入状态,神识悄然外放,却立即被阮芽逮个正着。
她拍桌而起,“干什么!敢偷看我牌?”
衔玉趁乱偷偷换牌,又被苗苗给擒住手腕,桌面一晃,阮芽的城墙砖倒了,她顿时大怒,“我好不容易才砌好的!”
柳催雪神识被她一弹,剧痛袭来,他心神不稳,心魔伺机而动,瞳仁倏地变漆黑,他冷哼一声,“那就都别玩!”话落两手一抬,把桌子掀翻了。
衔玉傻眼,这黑蛟登时妖性大发,一把操起戒尺,“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铲除你这邪魔!”
牌桌无亲友,这四人化作流光飞出,寻了个宽敞地打起架来,惹得一众凡人连连探头。
张梁一个头两个大,只能传音阮小花,希望她能过来主持大局,镇镇这帮无法无天的小年轻。
大婚当日,阮小花终于带着蓬英赶到,阮芽许久未见娘亲了,抱着她一个劲儿撒娇,要跟她脸贴着脸,手拉着手。
衔玉果然老实了,坐在一边,两手搁在膝头,板着个脸装老成。甚至连柳催雪都在想,这兴许就是他未来媳妇的妈的妈,他得跟着叫外祖母,或是外太岳母,得好好表现……
随后他看向蓬英,脸色一变,那蓬英岂不是又跟着涨了辈分?成他外公了?
柳催雪神情恍惚。
这就是命吗?
张梁散修一个,父母早已不在人间,苗苗是兔妖,生她的母兔子早几百年就变成干锅兔了。
是以婚礼仪式并不复杂,小两口拜了天地,一桌一桌敬完酒就成。
阮小花准备了丰厚的礼金,每个红包里装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简,玉简和金钞概念相同,是存灵石用的。
母女两个都喜欢玩叠高高,阮小花垒了个酒塔,每个酒杯上放一个红包,张梁和苗苗过来敬酒的时候,人都傻了。
阮小花笑眯眯,“给先生带了好酒,五百年的杏花白,一杯一个红包,每个五百上品,能拿多少,看先生本事。”
衔玉两眼发直,好多钱!
张梁视线环桌一扫,瞄准衔玉,趁机拉他下水,“帮帮兄弟,到手分你两成。”
衔玉之前还企图靠打麻将挣钱,后来因为不识数,算账老是算错,希望破灭,没想到下单生意这么快就来了。
他正要点头,阮芽大叫,“不行!”
张梁颇有遗憾,他实在不胜酒力,阮小花心真黑啊,那酒杯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一个快赶上他的笔筒大,真喝这么多,今晚上别想办事了。
谁知道阮芽下句接,“起码五成。”
衔玉反应过来,“对,这么多酒,才给我两成,你真抠门。”
张梁“哈”了一声,“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蓬英也跟着煽风点火,“你就说晚上还想不想洞房。”
苗苗脸都羞红,张梁一咬牙,“一半就一半。”
酒塔四层,共十九杯,杯底还有红包,共计二十七个,每个五百上品,衔玉算不出来,但单凭眼睛看也是一笔巨款了。
他话不多说,端起酒杯,张开嘴就往里倒。
阮小花恍惚间,想起自己上辈子见过的夜场歌手,那些家伙喝酒相当厉害,他们会把啤酒摇一摇,酒液呈螺旋状倒流,以此来加快喝酒的速度。
但都不如衔玉可怕,这可是白的!一杯起码装半斤,他张嘴就往里倒,甚至都不见吞咽,一杯酒就下了肚。
一时间,四邻都来围观衔玉喝酒,大家连话都不敢多说,生怕惊扰了他。
每喝下一杯,衔玉就揭下一个红包,喝完十九杯,他脸不红,心不跳,手背擦擦嘴角,平静道:“喝完了。”
阮芽掏出手帕,给他擦擦嘴,又擦擦手,扶着他坐下,“没事吧?”
衔玉摆摆手,“没事。”完了也不多说,两眼瞪着张梁。
张梁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给他竖个大拇指,“海量。”完事给他数了二十个红包摞在面前。
如果出事,就当医药费了。
衔玉满不在乎往阮芽面前一推,“收好。”
阮小花饶有兴味看着他们,推推蓬英,“感情真好。”
蓬英点头,“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阮小花说:“第一次见,是在万和城,那时候他们就像现在这样好了,明明才是第一次见面,可当时给我的感觉,却像已经认识了很久。”
蓬英思索片刻,“也许是前世的缘分?又或是月华果的关系?”
阮小花深感欣慰,“那还真是天生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