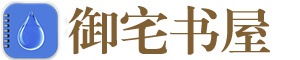前夕
作品:《玫瑰盛开时》 十。前夕
半夜,不知匿于何处的蝈蝈叫得十足响,比得上新制的铜铃,声音清脆持久。
天气闷热,后半夜,空气粘稠感愈发明显。
不知何时,一迭儿虫叫声消失,换来夜空滚雷,径直劈下,轰隆一声,惊得睡梦中人醒来。
四周一片漆黑,窗户半开,隔着纱窗望去,外头是灰暗色。倏得,一道闪电刺过,照亮半室,冷白凄清的光略过少女发愣的眼,随即,又是一个响雷炸裂。
雨来得很快,哗啦倾泻,打在树叶芭蕉上,敲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各种响声贯耳,此起彼伏,又交响呼应,虫叫自然就消声其中。
暴雨到凌晨才淅淅沥沥得见小。
揉揉太阳穴,单手覆眼,宁清柠懒散着坐起来。后半夜醒来就没怎么睡过,这下眼睛酸涩得不行,后脑勺也是一阵一阵痛。要不是约了今天量尺寸,这个懒觉她是睡定了。
早餐是青桔果酱配上黄金色吐司,青的青,黄的黄,嘴里一溜儿酸,一阵甜。她吃得胃口好了不少,虽然精神还是不佳,想打个瞌睡。
府上有特定的量衣房,半大不小一间,也足够宽敞。
隔门为雕花型,里层加了个蓝染花布,房内灯也好看,算亮堂又不致于刺眼,罩了个外壳的日光灯,光线温和。
量尺寸的是个比宁清柠岁数大不了太多的女孩,卷发,格子背带裤,皮尺挂在身上,一边量一边跟宁清柠夸她的老师怎样怎样有才华,是时装周的常客,得他一套私制的服装简直是人生罕事。
宁清柠转身,抽空跟她搭话。
“这么厉害?”
“嗯,老师早些年开始就不怎么做私人订制了,除了设计春秋周,其余时间都用在积蓄灵感和授课。”
“灵感要时时付诸现实才有意义啊。”
“老师说,没必要,不求名不求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
宁清柠等她记下最后一个数字。
“真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女孩收好东西,同她一道出门。
“你年纪小小,倒一副被世事磋磨过的模样,真是,好好享受当前——呐。”她说着,朝前方努嘴。
缓缓走来的是卓岸歇。
女孩又压低声音,“我当老师助手两年,从未见卓先生求过老师。你是例外。”她说的时候眼也别有意外眨了眨,此间含义,不消多说。
“人还给你了。”女孩说完就走。
卓岸歇抚额,笑了,觉得这说法很顺耳。
“衣服做好会送去你家。”他望着人,低眉说。
宁清柠“嗯”了声,不算清明的脑子过了过这句话,才猛地反应过来,“我妈妈来电话了?”
“是啊,留不住你了。”他不顾这是大庭广众,是随时会有人路过的走廊,伸手去牵她的手。软弱无骨,柔荑生香。
半夜的雨,清晨才停。
积了水的叶,叶面半边下垂,水顺着滚下,溅落在地面,滴滴答答的,静好的声音。
“我,见不到你了……”她低声,念了句。
卓岸歇捏着她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好笑得掂了掂,“我还以为你欢喜。昨日从书房离开,你就不甚开心的样子,眼神都是冷清的,我想你是念家,宁夫人来电话时,我就没拒。”
他叹气,收拢手,半是耳边厮磨的声音在说,“原来是我领会错了。”
宁清柠抬眼,眼眶微微泛着水红色,弄不清是缺觉还是别的原因,她问,“以后怎么办?”
不管你我之间是何种关系,也不管你怎么看待我,至少现在想知道,以后怎么办。
以后可以是下一秒,下一个时辰,下一天,甚至下一年,而未来不一样,时间跨度太广,她没有胆量去设想,也不敢问出口。
她知道这是“患得患失”的毛病,可得来太轻易,又如此没有情感基础,似乎就是她的一腔孤勇,被卓岸歇不知出于何种缘故逮住,便就此攥在手心,一边无所顾忌宠着她,一边又诱她越陷越深。
十八岁就遇见这样的人,不知是幸是孽。
卓岸歇来找她,其实是为了说今日一整天都没办法陪她。
要出门谈事情。
宁清柠被他牵着走,亦步亦趋,听到这话又停下来,眉头要并到一起,那双澄澈的眼,映入廊下光景,不发不语望了过来。
她困乏得不行,眼睛又干涩,之前情绪上了头,也憋得好好,这会儿听他的话,又太阳穴紧绷,生理的不适加之心中不舒坦,眼下,便烦意顿生,极欲冲破牢笼。
差点要堵着气冲他说,你快走,别在我眼前待着。
还好,垂下眼睑,忍住。
卓岸歇简直拿她束手无策,“好生生说着,你又变了脸,对我冷冰冰的样子,我又是做错了什么……”
“我本来就不好说话,你要不喜欢,我今天就回家去。”
这小孩儿说话的语气,卓岸歇听着想笑,又深知不能。他倒愿意,把这个张嘴就刺人的小姑娘抓进房,摁在身下亲,看她还会不会对自己冷冰冰,一副不欲搭理的样子。
“真是……看戏那天还记得吗,出门遇见一行人,打头那个男人算是卓家和许家一个合资企业下的拦路虎,打着坐享其成的念头,想抢我们开出的一条路。这阵子在应对他,所以拖不得。”
“清柠,我不是事业心过重的人,只是凡事必做好,要么就不做。”
“邀你来府上做客,还晾你两三次,这,还真是我不地道。”说着,无奈一晒。遇上她,把自己二十多年没道过的歉都道尽,但没办法,偏偏是她。他心里妥善安藏多年的人。
宁清柠听他好声好气,又舍不得生气。她嘀嘀咕咕,说给不知谁听,“你不地道的事,哪是这个……”
“嗯?你说什么?”他附身凑耳过去,笑吟吟问,明明听清也意会,还笑得那样坏。
气氛又开始变成烟楼半含雨,一层旖旎,一层绯色。多情催着入骨,雨也朦胧难辨。
一路亲密到房门口。路上稀奇,一人未见着。
宁清柠开始后知后觉,原来旁人无事不入东院,并非夸张。
她拍拍卓岸歇小臂,说,“你这人可真是霸道,不许别人随意进出此院就罢,家人也不可以啊?”
卓岸歇带她进门,手伸向她的细腰,不甚在意道,“他们大都不愿意亲近我,我能怎么办。”
“骗子!明明是怕你。”
被戳穿的人,依旧面色如常,还晓得脸靠近她,调戏她,“那你这是不怕我?胆子可真大啊。”
“我怕你干嘛,你又不会吃了我。”她红了脸,白净的皮肤,红起来活色生香,像刚熟的樱桃,初生的玫瑰。
“未必。”他又勾唇,笑出颠倒众生的样子。
宁清柠紧紧脱离他的手,不上他的当。
“你去忙,我补个觉。”
卓岸歇抱人的手,拇指抿了下食指,轻轻一摩挲,滑腻湿意,不知她从哪蹭过,惹来半臂雨水。
“赶我走?”他去捉人。
“我,我是真困,你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昨夜暴雨,被,就被吵醒了。”她被逼到床边。
卓岸歇将人圈进两手间,瞧她不好意思,瞧她因为自己红透脖子。
“那你结巴什么?”他越问越小声,也越凑越近。
停在她脸庞,他偏头珍惜得用唇滑过。
“睡吧,晚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