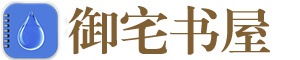卷十三 道别 (下)
作品:《相公出没注意》 莫说这是蚀骨之痛,在大刀穿越心扉时,她就已经血流不止。
不过……
「不用,是月缺失言。」朱唇微啟,如琉璃落地的清脆声音响起,盪在这偌大的书房中。
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湖泊般平静的瞳眸将激动封闭,唯一的破落是淌下无悔的绝望。泪花晶莹地闪烁,每一朵都写着她的无语与酸楚。
然而她不再拒绝甦醒。
她的手上,握有最后而最重要的底牌──
[i]「沁儿姐姐,宰相府如何?环境应该不比将军府差吧?」程月缺柔柔一笑,挥手退下她特意安排监视寧沁的侍女,落落大方地坐下,与寧沁彷彿间话家常。她没有怀疑寧沁的承诺,不过她不会参与没有把握的战争。
由发现寧沁是「骗子新娘」的一刻,她就知道她不可能会输。纵然她可能敌不过寧沁在莫言心里的地位,但是她能够将寧沁玩弄于股掌。
她可以巧妙地引导寧沁误会莫言,威胁寧沁离开莫言。以防万一,她更在寧沁揹着包袱离开将军府时将其带回宰相府软禁。
耗费心神,只为一个男人。
「程月缺,你到底想怎样?」寧沁气呼呼地看向她,却对上一双如狐狸狡猾的眼睛,完全摸不出头绪。
徐徐晚风跨越狭小的新月型窗櫺,温柔地抚摸着她吹弹可破的脸颊。她伸出頎长的指尖挪起一片香味浓烈的玫瑰糕,细味品嚐,对寧沁的问话毫不理会。
直至细小的嘴巴吃下整片玫瑰糕,才添上饜足的微笑。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
程月缺缓缓站起,脚步优雅地去到她的跟前,本来含笑的黑眸瞬间陌生起来,犹如长年藏身于雪山里的冰剑,成为冷冰且尖锐的利刃。她用力地扳起寧沁的下巴,漠视白晢脸孔的几道红痕,激动地问:「你是谁?你到底凭甚么褫夺属于我的东西?」
即便挣扎让程月缺在她的肌肤上留下渗血的微伤,寧沁还是不甘示弱地甩开程月缺的手。她忧伤地盯着程月缺,忽然觉得身为宰相千金的她十分悽凉。
「他不是东西。」连喜欢的人都当成死物。
程月缺嗤之以鼻的耸耸肩,失笑地说:「对,是人,一个会走会跑会思考的人。」就因他是人,她才没有办法轻易地将他弄到手。
可是,这并不代表她没有付出,亦不代表她不爱他。
「那又如何?他是属于我──程月缺的!」
属于吗?寧沁摇摇头,漾出蔷薇色彩的脣轻柔而坚定的呢喃:「不,他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即便莫言爱她,也不曾属于她。她不喜欢程月缺将她心里的大将军量化。
她对莫言,并没有具侵略的佔有,而是默默地守候。
程月缺不忿地捡起第二片玫瑰糕,像是听不习惯寧沁的大义凛然,浑身气得不自在的发抖。这算甚么?爱他不外乎为了得到他,就算硬拼都要抢回来,她就不相信当她将莫言据为己有,寧沁还能泰然自若。
「……沁儿姐姐,你敢与我赌一把吗?要是我输掉,我可以放你走,你要回去言哥哥身边也行,要离他千里远也行,我绝不干涉。」她的嘴角牵起一丝阴森,脑海里錙銖必较的算盘已经计算出对她双赢的法子。
这局,她要寧沁再无翻身之日。
寧沁暗暗地吁了口气,不置可否地问:「你想赌甚么?」
「就赌你对他的重要性。」
程月缺的脸承戴浅浅的笑意,准确无误指向寧沁,如同无邪的孩童玩着无伤大雅的游戏。不过,唯独她明白,不论寧沁对莫言是否举足轻重,她都有权随时改变游戏规则。
她才是控制赌局的庄家。
「如果失去你,他决意终生不再娶,就算你胜出。反之亦然。输了的你必须向官府自首。」
寧沁深深吸入空气,心湖很平静,彷彿他就在她的身边支持她、鼓励她。
「好!一言为定。」
眼见寧沁天真地答允,她心里狂喜窃笑。寧沁输了,她当然能够大条道理将其送入官牢;要是寧沁获胜,心情欠佳的她同样可以更改约定,将寧沁丢入狱中。
虽然这刻她亦有能力将这口眼中钉拔除,但是她享受只有一半机率的刺激。徘徊在胜负的边缘,方能显出她的临危不乱。
不过,她就是胜利。[/i]
──没错,她梦醒了。她要赶在一败涂地前,拾回属于她的胜利。
「言哥哥,月缺就此拜别,还有一点事情需要处理。」程月缺迈开步伐,沉重地朝门走。她对寧沁憎恶,却欣赏寧沁始终光明磊落,更是妒嫉寧沁和莫言之间的信任。
她注定闯不进他俩的天地,便只好选择破坏这个空间。
「……月缺。」
当程月缺的一双柔荑已经伏在门柄时,莫言叫停了她。
她本不想停下来,双腿却不争气地变成铅块,教她无法提步。
「……抱歉,还有谢谢你。」
莫言一动不动地凝视她的背影,从此程月缺终于走出有他的世界。他相信他们不会再有交集,可是若说他对程月缺没有感情绝非事实。他们曾经亲厚的兄妹情谊,铁不是虚假的。
「希望言哥哥能尽快找回沁儿姐姐,一家团聚。」
最后一刻,他不是狠心地将她赶走,而是礼貌地道别。她低头望住握得发白的双手,宛如覆上一层朦胧的薄纱,模糊得光是轮廓都显得格外含糊。
「再见,言哥哥。」
她推门而出,心里但愿他是狠心的将她驱赶。这样的话,她才有恨他的理由,以后所作的事情才会有意义。